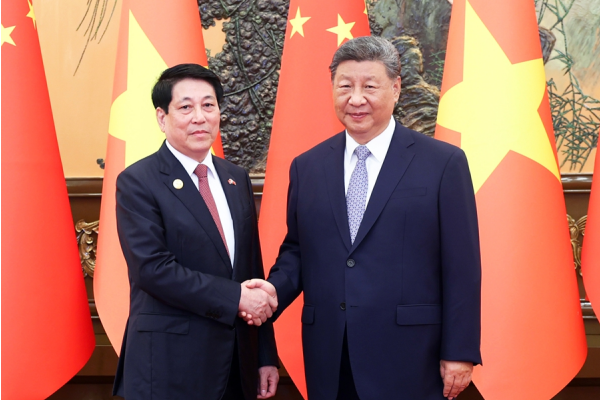高誓男/中央警察大學兼任教師
新修《憲法訴訟法》(以下簡稱《憲訴法》)於本(2025)年1月25日生效,民進黨政府遵循炮製「立法院國會改革案」,由該黨立法院黨團依賴清德總統公告批示,認有影響憲法法庭正常運作、侵犯司法權力,於23日第2度向憲法法庭提出暫時處分及聲請釋憲。這個舉動也再度受到關注,引致正反批評。然而,根據《憲訴法》,憲法法庭的大法官出席人數「不得低於10人」,目前大法官僅有8位,將無法執行審判。
司法審查的本質:憲政對抗民主的矛盾
現代民主憲政國家,國會立法權代表民意,法律(包括憲法)由多數制定,代表主權在民、民主統治;法院司法權適用法律(包括憲法),必須依法獨立裁判,以保障少數權利,此意謂憲政及法治,兩者在本質上有相互衝突之處;尤以大法官解釋憲法的司法審查權為然,從而司法審查權在學理上被稱為「抗多數機制」(counter majority)。
民主及憲政同為現代文明國家的重要原則,但在權力分立政府,分由不同的權力機關來行使,並根據不同的政府體制存有互異的競合或制衡關係,一個政府是否具有司法審查的制度,即影響立法與司法的關係。擁有強勢司法審查的政府,司法權不但分享立法(決策)權,也對立法權發揮強力的制衡(侵襲)作用,可能限制民主的體現;但弱勢或不具司法審查的政府,則立法權較能展現多數的民意、發揮民主的功能。Jan-Erik Lane等學者即指出,那些採行民主制且僅承認弱勢司法審查的國家,才是真正的「憲政民主國」,如英國、美國,這種司法機關也被稱為「最小危險部門」(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司法國(強勢司法審查)的危機
我國法制主要繼受大陸法系,司法審查機制亦然。而揆諸大陸法系國家的代表者德國,其司法審查法制幾經演變,不論就理論或實務來說,幾乎沒有甚麼審查「界限」可言,儼然已經成為強勢司法審查制度的代表,所以才有「司法國」之稱。就我國大法官釋憲近幾年的實務發展而言,較之德國也不惶多讓!唯一不同的是,我國的發展有著更多「政治化」的色彩。
過去8年蔡英文政府時期,執政黨完全執政並可壟斷大法官人事,大法官的解釋無一不與政府政策契合,任何對抗政策的憲法訴訟,如107年的年金改革法案釋憲,無不全軍覆沒,導致大法官立場偏頗的質疑。這種司法「政治化」的趨勢,不僅是種下今日朝野政治對立及矛盾的主因,也導致民眾不信賴的「司法國」(Justizstaat)危機。
《憲訴法》的前身是《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當時也是以三分之二作為可決人數門檻。2022年舊《憲訴法》上路後,才將判決的門檻調降到大法官現有總額二分之一,希望透過制度調整,提高審判效率。如今門檻又調回三分之二,且增加違憲時需有至少9位大法官同意的規定,在野黨認為,提高門檻可讓大法官判決更具正當性。就制度設計而言,兩種門檻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政策價值的取捨,即審判效率及判決共識孰輕孰重的立法裁量問題,沒有涉及是否違憲。
眾所周知,之前立法院上演的大法官任命僵局,一方面是總統提名人選不符合在野黨期待,另一方面也受到國會職權修法的釋憲結果影響,以致在野黨對現任大法官產生更多不信任,才透過修改《憲訴法》,達到影響憲法法庭的效果。針對目前的民主憲政風波,朝野雙方都有責任。
大法官球員兼裁判若對《憲訴法》解釋 是憲政危機
綜合前述,我國如要確立真正的民主憲政體制,建立什麼樣的司法審查制度應是重中之重。如果朝野政黨不能從理性的制度設計思考出發,而欲一味進行赤裸的政治角力,則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憲訴法是大法官行使職權時所依據的法律,但當大法官審查法律是否違憲,該法律涉及大法官的權限或程序時,如大法官甘冒「球員兼裁判」之嫌,堅持適用有違憲爭議的法律做成決定,這個決定本身是否也有違憲的可能?則大法官要做這樣的宣告違憲,就不只是冒著法律上的風險,更有政治上的風險,可能進一步被立法委員報復,面臨到的政治反作用力將更大。
總之,就維繫民主憲政的價值而言,大法官在憲政體制中有其重要性;但若無法保持應有的獨立及中立性,並恪守適當的司法自制,就有可能侵犯代表民主的立法權;一旦再淪為政治對抗的工具,其戕害民主的後果更無法想像。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梅花專論】民進黨政府操弄憲政對抗民主造成憲政危機

總統府23日公布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前中)、幹事長吳思瑤(右)等人向司法院遞交暫時處分及釋憲案。圖/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