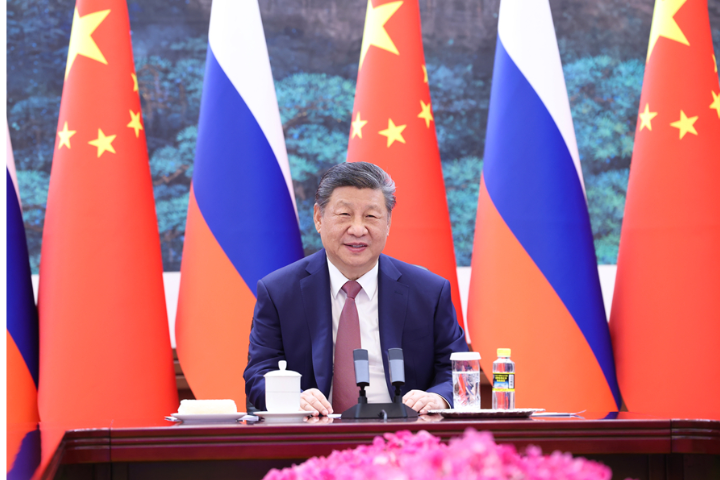楊泰順博士/中美文經協會理事暨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預算不能增、內容未先審 預算淪為菜場喊價
立法院大刪政府預算引起執政民進黨強烈不滿,配合民團於全台各地發動罷免藍營立委的行動;為了反制,在野黨也點名幾位綠營立委進行罷免連署,台灣社會的對立被升高到前所未有的緊繃。
國會看緊政府荷包卻導致社會的嚴重對立與立委面臨罷免,筆者前文已指出這與台灣憲政僅賦予立院預算刪減權有關。由於不能增加預算或變更預算項目,朝野審查預算時便無法進行數字背後的政策辯論,使得言語謾罵充斥於審查過程。此外,預算中的各計劃項目,編列前並未經立院討論與授權,在野黨立委在不明瞭計畫內涵下,刪減時難免顯得任性,例如統刪10%由行政單位自行調節便是一例。
立院的預算審查決議其實包含兩類處理模式,一為直接刪除編列預算,如刪除各部會媒體文宣費,與數位部、NCC、陸委會等的業務費,及台電補助款一千億元等,便屬此類;另一則為「凍結」預算,如各部會業務費先行凍結70%,潛艦國造凍結10億元等。預算刪除將難以回復,對部會的運作必然造成困擾,至於刪除是否合理乃屬仁智互見,如拿納稅人錢補助台電虧損造成市場機制扭曲便有討論的空間。但筆者認為,在立院功能殘缺的狀況下,凍結預算的作法不僅合理,甚至有其必要性。
監督政府財政是民意機構的天職,政府為了預算案能順利通過,往往會將金錢用度被包裝得重要又必要。但預算一旦通過,這些錢是否被暗度陳倉或變相使用,民意機構既非執行者又不能指揮情治體系(尤其國會擴權法案又遭擱置),想要有效監督幾乎不可能。此次在野黨全數刪除各部會的文宣費用,便因發現這類經費不少被用於攻訐在野黨或酬庸執政者的側翼組織。但全數刪除並非妥善的作法,如警廣與國光客運的文宣費受到池魚之殃,便被執政黨拿來指責在野黨罔顧民生安全。
GAO協助美國國會監督經費使用
以美國為例,為了有效監督政府的預算使用,國會下設一個擁有五千位專業幕僚的「政府課責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對政府經費是否合理使用進行全天候的嚴密監督,為國會最龐大的幕僚機構。筆者在前文已提過,由於國會希望整合政府預算編列,乃於1921年通過會計法案,將預算案脫離其他法律案,授權由總統負責編列提出。但國會也擔心行政體系會上下其手玩弄數字,乃在法案通過時同時設立此一部門,負責緊盯預算的使用狀況。該部門既以審查政府經費使用為目的而成立,故原稱「總審計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但運作近百年後,國會發現GAO並不只是查帳了事,還會對經費使用效率與合理性進行檢討,並做為議員來年審查預算時的依據,於是在2004年更名為「政府課責署」以求名實相符。
審計權歸監院 殘缺立院只能凍結預算
可惜美國行憲史上這項寶貴經驗與邏輯,並未獲得中華民國憲法的立憲諸公重視,為了貫徹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竟然將政府的年度決算權歸屬於監察院的審計部。眾人皆知,小至家庭大至國家,財務管理除了預算審查外,檢討經費使用的事後決算權也是不可或缺,沒有決算權又如何佐證預算編列是否合理?台灣經過數次修憲,監察院既非民意機構也非獨立機關,而常被歸類為執政黨的酬庸單位,由如此性質的機構掌握決算權,民意機構又如何能履行其看緊政府荷包的天職?台灣憲政將審計部獨立於立法權之外,似乎是為了行政權獨大而有意搞殘立法院,將今天國會的亂象視為全民共業恐怕並不為過。
缺乏決算權及監督預算執行的權柄,「凍結預算」似乎已是立院履行其職責不得不然的選擇。根據立院所通過的決議,相關單位必須在執行30%業務費(潛艇則待海測)後,向立院報告使用狀況,才能由立院決議解凍剩餘的70%預算。此一作法當然有些粗糙,但在立院功能殘缺的狀況下,非如此又如何能有效監督納稅人錢不會被濫用?民進黨往後若淪為在野黨,相信應該也會循此策略,監督執政黨是否將錢花在刀口上。當然,釜底抽薪之計,便是藍綠合作再次修憲,將審計權回歸立法院,讓台灣有個功能完整的國會。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