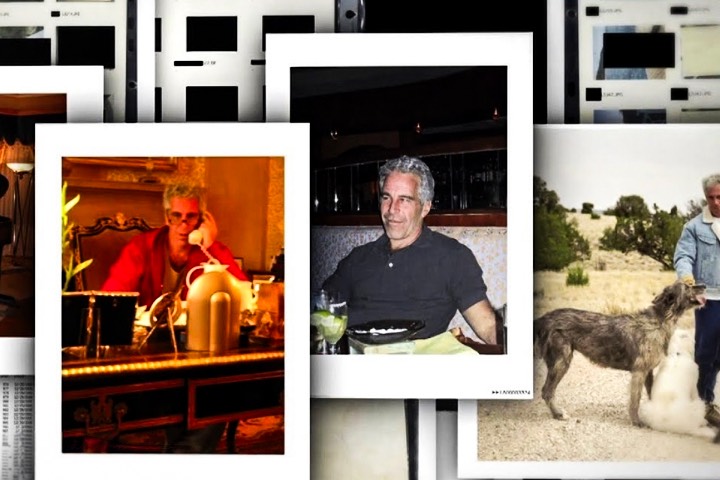李貴敏/現任律師
截至2025年4月,全台同時背負房貸與信貸的「雙貸族」人數飆升至39.8萬人,創下歷年新高。這不僅僅是一串冰冷的數字,而是無數家庭故事的縮影,是一個世代在經濟壓力下掙扎的真實寫照。從2012年到2019年間,雙貸族人數彷彿一潭平靜的湖水,始終徘徊在28萬至29萬之間。然而,近年來卻暗流洶湧、拍打上岸,並掀起令人措手不及的巨浪。雙貸族為了換取一個棲身之所,把自己的未來也押上了!
媒體報導顯示出,年輕人即便月薪16萬也不敢生小孩,行銷工作者就算一天三份工,也存不了錢?有誰願意在大好青春年華裡,為了一處遮風避雨的地方,把生活拆成碎片?又有誰想在剛起步的職涯裡,被迫進行高槓桿操作,押注一個前景未明的未來?這些選擇究竟是出於貪婪?還是生存的無奈?這些又是社會的特例?還是這個時代的普遍寫照?
其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在其著作《非理性繁榮》中已點破這樣的情境。人們在資產價格飛漲時,容易陷入集體性錯覺,誤以為這場繁榮將永無止境,而忽略風險。以買房為例,房價每創新高,就像催眠般,讓人以為「現在不買,以後更買不起」,房價一次次創下新高,宛如一場催眠,讓人們在恐懼與貪婪的交錯中,越陷越深,終至債務泥沼。這一場場自我強化的泡沫循環,更讓無數家庭在追逐夢想的路上,背負沉重的代價。
令人憂心的是經濟學者明斯基(Hyman Minsky)的「金融不穩定假說」表示:經濟長期穩定容易讓人低估風險,過度借貸,直到某個臨界點,連鎖反應才會爆發出來。因此,當利率緩步升高,當房價出現修正,當信貸收緊,雙貸族的脆弱資產負債表便再也撐不起表面上的穩定。這個所謂的「明斯基時刻」,或許不會在一夕之間吞噬整個經濟,卻會像滴水穿石般,逐步侵蝕社會的中堅力量。
雙貸族的爆起,反映的不是單純的經濟波動,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壓力積累。在超高齡社會的陰影下,在少子化的寒風中,台灣人面對的不僅是當下的房貸與信貸,還有未來的長照責任、停滯的薪資,以及日益僵化的就業市場。從一對年輕夫妻到「三明治世代」,他們上有老、下不管有無孩子,中間還要硬撐著貸款與生活的重擔。在這樣的處境下,即便財經數據亮眼,政策文宣動聽,也掩蓋不了共同的體感:生活越來越難,夢想也越來越遠。
仔細回想,雙貸族的增加,就是「以債養債」的生活方式成形所致。倒未必是人人都想當投資客,更多是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家。因此,當購屋門檻水漲船高,當頭期款變成夢中遙不可及的數字,他們只好動用信貸,補足那最後一哩路。但這條路卻是愈走愈險,也愈走愈窄,更成為一條難以回頭的債務長征。
然而,政府的政策卻總是牛步前進,還往往失焦。就拿限貸為例,表面上看似打擊炒房,卻推高了首購族的資金缺口;再拿生育補助為例,即便再三加碼,卻忽略育兒與購屋的制度性成本,遠非幾萬元的紅包所能解決。當民眾為一點喘息空間苦苦掙扎,政府卻沉迷於政治鬥爭的喧囂,將民生疾苦消音成背景雜訊。政治的熱鬧與經濟的蕭條,形成了一幅詭異的對比。
然而,民眾並未忘記生活的真相。上個週末,他們用選票發出了最響亮的聲音,展現了更大的民主。不是因為誰講話更大聲、口號更動聽,而是因為他們明白,過去一年這個國家太熱衷於撕裂、動員與鬥爭,卻始終無法好好安頓人心。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用最安靜的方式說出了最響亮的話語:我們不是非理性繁榮中的配角,也不願成為明斯基時刻的犧牲者。他們用行動,訴說了一個簡單卻沉重的願望:一個公平的社會,一個有希望的明天。若這樣的願望,在當下仍顯得過於奢侈,那麼,我們必須追問:是誰讓一個世代的夢想,變得如此遙不可及?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