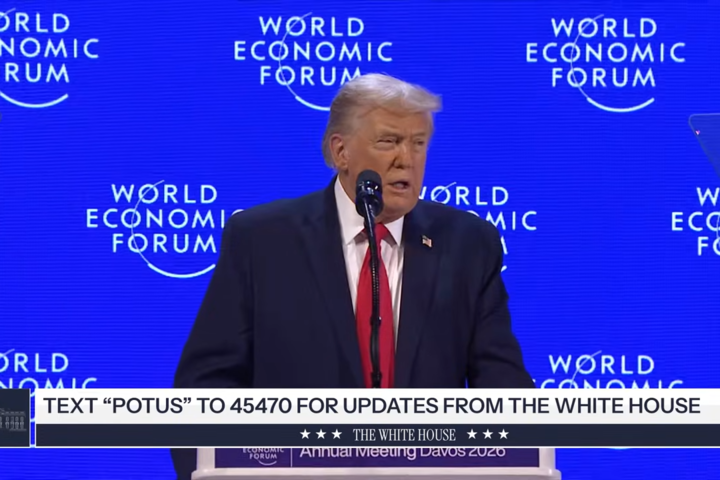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安全政策的異化危機
在冷戰結束後,美國自視為自由秩序的守護者,其國家安全政策傳統上奠基於軍事力量、外交網絡與制度規範。然而,近年來卻逐漸浮現出一種令人憂慮的趨勢:安全政策日益被財務利益與產業壓力所綁架,甚至淪為政府和企業可交易的資產。據前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小唐·格雷夫斯(Don Graves)與其經濟和國家安全高級顧問阿魯普·穆哈吉(Arun Mukherjee)於9月24日在 《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共同發表《National Security for Sale》的文章指出,美國政府愈來愈頻繁地將出口管制、軍售與高科技授權設計成一種籌資工具,安全與利益的界線正被快速侵蝕。
本文將依該論述分析美國國安政策如何被「利潤邏輯」扭曲,並探討其對戰略、制度與地緣格局的深層危害,最後提出若干矯正方向。總體核心觀點是:當國家安全成為金錢遊戲的一部分,短期回報將凌駕長期戰略,最終削弱美國的制度信任與國際地位。
出口管制的財政化
高科技產品出口長期是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工具,原意在於限制敏感技術流向潛在對手,例如大陸。然而,格雷夫斯與穆哈吉指出,美國政府逐步將出口授許與財政收益掛鉤,設計出某種「抽成」或「收益分享」機制。企業若願意上繳部分營收,即可能取得出口許可。
這樣的做法讓授許決策被財務利益滲透。官僚體系傾向於批准更多交易,因為每一次核准都能轉化為政府收入。短期內或許能補充財政缺口,但長遠來看,風險評估被迫讓位於金錢考量,可能導致技術流失與安全隱患。
一旦這種模式形成路徑依賴,任何收緊管制的建議都會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反對。管制從戰略工具逐漸淪為財政手段,這正是制度扭曲的開始。
軍火工業與安全政策的共生
軍售本是外交與安全戰略的延伸工具,但在美國,它同時承載龐大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冷戰期間,美國對沙烏地阿拉伯的軍售案例已顯示,經濟與能源利益往往凌駕於純粹的安全考量。
進入二十一世紀,軍售的影響力更深。每一筆大型軍售交易背後都是數十億美元合同,牽動國內的產業鏈與就業市場。國會議員因選區工廠與就業而積極推動軍售,這使得安全需求被包裹在利益計算之中。
軍售逐漸演變為一種「外交與經濟雙用途」工具。問題在於,當利益凌駕戰略判斷,美國可能低估軍售對地區局勢的長期破壞性後果。
政府投資與股權干預的隱憂
除了軍售與出口管制,近年美國政府也透過創投基金、補助與股權參與直接介入高科技企業。名義上,這是為了確保在半導體、人工智慧與量子科技上的優勢。然而,當政府同時是監管者與投資者時,利益衝突問題就浮現出來。
政策可能因政府的投資利益而偏向特定企業。例如在研發補助、國防標案或監管鬆緊上,決策會受到資金回報的影響,而非單純的戰略需求。這削弱了市場機制,也讓部分企業養成依賴政府的習慣。
如果國家安全與股權收益過度綁定,整體產業將逐漸失去競爭活力。表面上看似保障技術優勢,實際卻可能讓創新生態變得僵化。
利益扭曲的深層危害
將安全政策當作利益交易,後果遠超過單一決策本身。最直接的問題是戰略風險被壓低。當財務回報被放在首位,技術外流與軍售反制的潛在威脅反而被忽視,長期優勢被逐步侵蝕。
更進一步,制度也可能出現腐化。企業若知道出口許可與收益掛鉤,就會加大遊說甚至採取不正當手段,導致決策透明度與問責性下滑。公眾最終會發現,安全政策是「用錢買來的」,對政府的信任隨之下降。
地緣政治影響同樣不可忽視。盟友與對手都能看出美國把國安政策當成交易籌碼,這會讓談判桌上的籌碼逆轉,甚至讓美國陷入被動。
矯正與重建的可能路徑
要遏止國安政策商品化,必須從根本制度切入。出口授許應徹底脫離「收入來源」角色,只能依風險評估決定,避免形成財政依賴。
同時,國會與獨立機構需強化監督。透明度越高,企業就越難以用利益輸送影響政策。智庫與媒體在此也能發揮外部制衡的力量。
政府對企業的介入應有所邊界。補助可以存在,但股權控制須謹慎,並建立退出機制,避免讓國安與投資回報混為一談。
此外,對敏感技術和軍售應建立跨年度戰略評估機制,讓長遠風險被制度化檢驗,而不是任由短期政治或財務壓力主導。
結語:別讓國安淪為利益遊戲
格雷夫斯與穆哈吉的分析揭示了一個現實:當國家安全被包裝成交易商品,戰略判斷就會被財務邏輯侵蝕。出口授許、軍售與政府投資若繼續朝籌資工具演變,美國的制度信任與全球地位將難以維繫。
矯正的關鍵在於制度重建,包括脫鉤財政與安全決策、強化監督與透明、限制政府投資角色,以及建立長期風險審查。唯有如此,美國的安全政策才能回歸本質,不是金錢遊戲,而是真正守護國家利益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