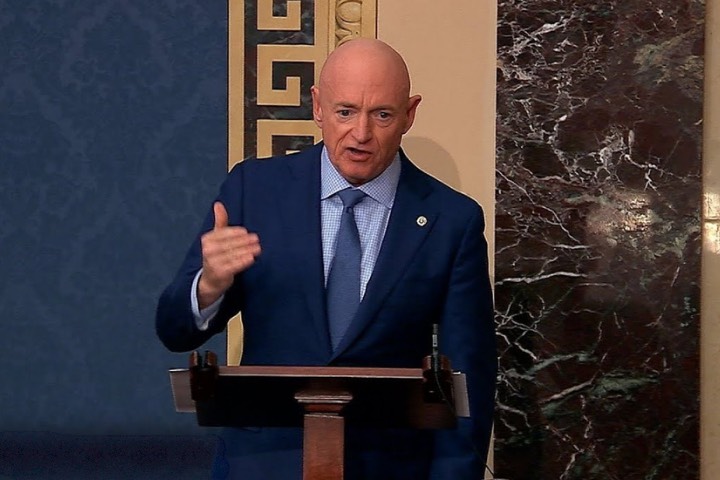羅光達/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台灣在面對國際情勢的劇烈變化下,特別是與美國在科技、經貿、軍事的複雜關係中,除了地緣政治所帶來的挑戰外,也正面臨一場潛在的財政考驗。
根據美國媒體Politico的報導,在我國最新的對美關稅談判中,川普政府要求未來對美投資金額將介於3,500億美元至最高可能達5,500億美元的規模(約新台幣10.85兆~17.05兆),類似美國對韓國、日本的模式。這代表台灣在未來數年必須在美國大規模投資,以符合談判條件,從而確保關稅協定的達成與貿易穩定。
可預見的巨額財政支出構成嚴峻挑戰
除了上述這筆龐大的金額外,若再加上為了因應美國關稅衝擊而編列的特別預算,以及規模預計上看新台幣九千多億元的國防預算,三者合計的巨額支出,無疑將對我國的財政永續、總體經濟乃至國家戰略佈局,構成嚴峻的挑戰。
台灣當前面臨的財政挑戰,並非僅單純的政務支出增加,而是源於三種性質不同但具有高度政治連動性的支出需求。
首先,傳聞中至少3,50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要求,其金額規模遠超過台灣歷年的總預算規模,甚至占了2024年我國國內生產毛額(GDP)40%以上。雖然行政院立即表示「台灣模式」與日、韓投資模式不同,無法直接比較,且相關訊息未經證實,但此一數字確已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這筆支出本質上是為了換取美國在其片面加徵的「對等關稅」上讓步,以維繫台灣出口的競爭力,具有「談判籌碼」的性質,而非傳統的一般政務支出,其效益難以量化,且一次性投入的風險極高。
其次,為因應美國「對等關稅」的衝擊,行政院曾於2025年4月提出《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國土安全韌性特別條例》草案,擬在上限為新台幣4,100億元下,協助受關稅戰衝擊的產業進行研發轉型、拓展國際市場,並提供金融支持。後經立法院2025年8月審議修正通過,除將名稱調整為《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外,亦將預算上限提高至5,700億元。這項支出本質是「救濟扶助」的性質,用於穩定社會民生和產業結構,必要且緊急,但必須確保其效益能夠真正幫助企業轉型而非僅是短期補貼,否則長期補貼下可能扭曲市場競爭機制,影響產業轉型效率。
最後,在中共軍事威脅與美國要求下,國防部傳出將推出規模上看新台幣9,450億元的軍事預算,增加對美採購飛彈及無人機等,以強化我國作戰能力,這將是中華民國歷來最高的軍事特別預算規模。在當前區域安全情勢下,這項支出被一些人視為不得不為的「國家安全」投資。然而,必須確保每一筆預算都用於符合不對稱作戰精神,以及可以有效提升戰力的項目。
「戰略投資」不能造成影響永續性的「財政黑洞」
我國目前雖然要先面對來自國際政治與安全局勢的直接壓力,但長期也勢必面臨對國家財政間接造成的重重考驗。從談判籌碼、救濟扶助到國家安全三個面向的「戰略投資」,是否會造成「財政黑洞」的結果,是我們必須要審慎思考的問題。
首先,財政的永續性將面臨考驗。龐大的外部投資承諾與軍購預算,意味著未來幾年中央政府必須持續大量籌措財源。若政府的稅收基礎擴張速度未能與支出規模同步增長,國家財政將面臨入不敷出的結構性風險。一旦支出長期依賴舉債,債務壓力將急速攀升,不僅可能擠壓未來的財政彈性,也可能進一步債留子孫。
此外,來自於對產業核心競爭力的衝擊也是一大問題。即使「台灣模式」的對美投資主要由民間企業主導,但若其金額巨大且帶有非市場性的強制意味,實質上是一種「政治性」的資本流動。這將使台灣如半導體等優勢產業,被迫把更多高價值製程、研發與高階人才轉移至海外。長遠來看,這不僅造成國內產業結構空洞化,加速人才流失,更將從根本上削弱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和經濟動能。
再者,大量依賴特別預算來應對危機與採購,衍生出使用效率與透明度的制度性問題。特別預算相對較缺乏年度總預算的嚴謹審議程序,使得財源分配較易產生不均,並可能因為缺乏有效監督而導致浪費,進一步加劇社會對財政分配的不滿與質疑。
公共政策項目預算的排擠效應難免
最後,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來看,龐大的軍事支出雖然是維繫國家安全的必要之舉,但勢必也會對其他重要的公共政策項目,如教育、社會福利、公共基礎建設等構成嚴重的排擠效應。
因此,政府在面對現今的國際政治壓力時,必須跳脫只是單純的「危機應對」思維,更應將財政規畫提升為一項戰略性的資源配置。在積極籌措財源的同時,必須確保產業投資的自主性、提升特別預算的使用透明度,並審慎衡量軍事支出與民生發展之間的平衡,謀求一個更為精準與平衡的財政策略。(本文為作者觀點,與啟思民本基金會無關。)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