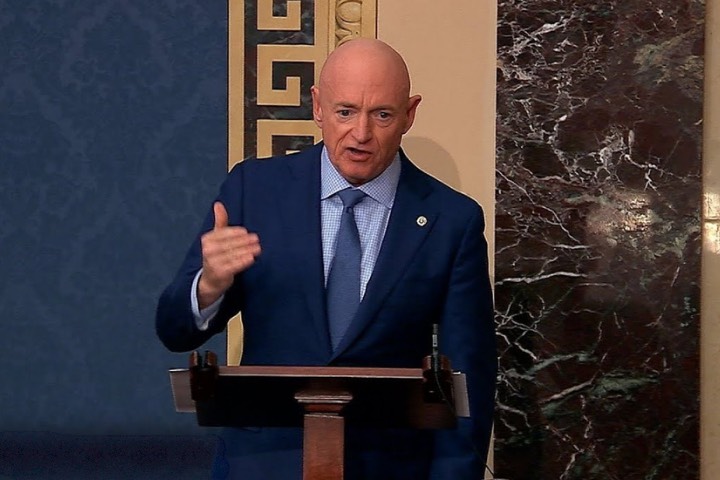陳國祥/資深媒體人、前中央社董事長
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政治經濟景觀正經歷一次巨大的結構性重塑,而這場重塑的主軸無疑是中國與美國之間長期且不可逆的競爭關係。兩強競爭已不僅是軍事上的對峙、外交上的博弈或科技上的追趕,而是一場全方位的深層競爭——競爭的是制度設計、產業組織、創新能力、能源體系、供應鏈控制力、社會心理韌性,甚至是各自的歷史敘事與文明吸引力。
中國在其中所展現的多維度優勢,使其成為美國難以壓制的對手;但中國所面臨的內部矛盾與外部壓力,也讓其崛起之路充滿不確定性。
從產業體系的完整度,到科技創新的突破性;從能源與基建的巨大投入,到供應鏈韌性的全球延伸;從人口結構與內需困境,到制度激勵與全球治理能力,中國競爭力的每一層面都既展現強處,也暴露短板。理解這些深層結構,是理解中美競爭大局的基礎,也是推估未來國際秩序走向的關鍵。
擁有完整而龐大的工業體系
中國今天之所以能在國際競爭中展現超乎想像的韌性,根本原因仍來自其完整而龐大的工業體系。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全部工業分類的國家,這意味著它擁有從原材料、設備製造到終端產品組裝的全鏈條能力。這種「從螺絲釘到高鐵」的全套工業實力,使中國在全球供應鏈重構的浪潮中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因為其不可替代性而重新獲得戰略位置。
美國多年來試圖推動供應鏈遷移,但越南、印度、墨西哥雖然承接了一部分產能,卻無法擺脫對中國上游零組件、設備與原材料的依賴,這種「迂迴供應鏈」反而更加凸顯中國的結構性重要性。
更關鍵的是,中國的工業體系正在從「大規模的世界工廠」轉向「高技術的世界工廠」。高技術製造業的增長速度明顯快於整體製造業,工業機器人、數控設備、新能源車、電池與光伏設備的產量既創下全球紀錄,也形成新的外溢效應。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能吸收大量產品,也能在產品迭代初期提供真實而巨量的使用場景,形成市場拉動技術的獨特路徑。
新能源車就是最佳例子,中國市場讓企業在十年間完成歐美廠商需要二三十年才能達到的學習曲線,使得比亞迪等企業得以在全球拔得頭籌。這種「技術+市場」的複合紅利,是中國製造體系持續升級的關鍵。
中國的產業優勢不僅止於工業深度,而是與高速基建與能源供應體系形成互相強化的正向循環。中國的電力供應占全球約三分之一,在火電、風電、核電到光伏各領域均具巨大規模,其中光伏裝機與風電裝機多次刷新世界紀錄。這意味著中國能為AI運算、數據中心、雲服務、先進製造提供相對低成本且穩定的能源,而這在AI時代將越發重要。美國雖然有高科技人才與大型科技公司,但其老化的電網與電力成本已成為AI擴展的瓶頸;中國的能源結構則更利於新產業的規模擴張。
基礎設施領域更是中國競爭力的另一核心。中國擁有全球最長的高鐵網、最密集的高速公路網、最具效率的港口群與最快速的5G建設能力。這些基建不僅改善內需經濟,更重新編織亞洲乃至歐亞的物流版圖。一帶一路沿線多國因中國承建的港口、鐵路、能源站而融入新的區域價值鏈,使中國在全球供應鏈治理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這是一個長期效應,而非一時的經濟刺激。
從追趕到並跑甚至領跑
中國快速崛起最受關注的領域仍是科技創新。中國多年來從「追趕」轉為「並跑」,如今在多個領域已具備「領跑者」的特質。從量到質的變化在全球創新指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中國的科技創新集群數量首次超越美國,並由深圳—香港—廣州取代舊金山灣區,成為全球第一科技集群,這是歷史性的結構轉折。
AI領域更凸顯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DeepSeek 等企業以低成本訓練策略、模型壓縮技術與開源路徑打破傳統美式算法邏輯,顛覆了「算力等於實力」的想像,使全球AI競爭從硬體主導轉向軟體與算法主導,這是一場路徑革命。
科技創新的另一個關鍵,是中國將技術迅速轉化為能大規模商業化的產品或服務。從外賣物流系統的全國普及,到AI在城市治理、金融審核、醫療診斷的日常應用,中國社會的科技接受度、使用密度與場景多樣性構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應用型創新環境”。如果美國的科技是由創投與科研驅動,那中國的科技則更由市場與社會場景驅動。這種路徑並不尋常,卻具有強大勢能。
但中國的科技崛起也有其明顯天花板,半導體製造仍是最核心的短板。中國在AI算法上具備突破能力,但在高端晶片上依賴進口,高階製程受限於美國封鎖。中國的科學家與工程團隊確實在制程設備、光刻機、材料等領域努力追趕,但距離全球最前端仍有明顯差距。這是中國不可逃避的結構性問題,也是美國在戰略上最希望抓穩的「卡脖子」點。
掌握全球產業的節奏
科技之外,中國的供應鏈擴張也進入新階段。早期的中國製造外移多是生產基地向東南亞轉移,但近年的趨勢已明顯不同——中國企業不再只是外移產能,而是輸出整套技術、標準與管理能力,使供應鏈成為一張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網絡。印尼的電池工業園、墨西哥的汽車供應鏈、匈牙利的電池廠都顯示,中國企業透過海外投資不僅佔據市場,更將自身轉化為全球產業布局的規劃者。這使得中國不僅掌握生產能力,也掌握全球產業的節奏。
然而,中國的競爭力強大之處,也往往是全球緊張局勢的來源。中國的高效率、低成本與高速擴張,使美歐企業無法在市場上公平競爭;而中國龐大的產能輸出,被美國視為對其工業基礎的威脅,因此出現關稅、制裁、反補貼調查、各種去風險化政策。中國的供應鏈優勢因此成為一種被戒備的力量,反映了地緣政治不信任的加深。對外,中國面臨圍堵;對內,中國也面臨結構性矛盾。
最深層的挑戰正是這些內部矛盾。半導體困境之外,產能過剩問題越來越明顯,尤其在新能源車、光伏板、鋼鐵、水泥等領域。中國的制度激勵仍偏向以規模換速度,使企業往往陷入「加速擴產—價格下跌—利潤下降—再擴產」的惡性循環。地方政府為了GDP、稅收與就業,也不斷刺激投資,使過剩問題一再累積。這些矛盾並非當前才出現,但如今在全球需求放緩與市場飽和的情況下,變得更加尖銳。
更複雜的是,中國內需長期疲弱、房地產泡沫破裂、人口老齡化加速、青年失業率偏高,使消費與投資雙雙承壓。民營企業在監管風暴與政策不確定性下信心受挫,創投資金撤離,使中國由創新驅動逐漸回到資產驅動的模式。這些都是中國面臨的長期瓶頸。
競爭力必須的延續寄託於結構性改革
因此,中國的未來競爭力能否持續,取決於是否能進行新一輪結構性改革,並在國際秩序中扮演更積極角色。中國若能真正讓創新取代產能擴張,讓制度激勵引導資金流向高附加值領域,讓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中扮演核心角色,讓外部世界在供應鏈合作中形成信任,那麼中國的崛起將更扎實、更持久。
反之,如果中國無法在制度、經濟、科技與國際合作中找到平衡,則即便規模優勢再大,也可能因內部成本上升與外部阻力增強而逐步消耗競爭力。中美競爭已是一場長期戰,中國未來的強弱,不僅取決於是否能維持已有優勢,更取決於能否化解那些正在增長的內部壓力。
世界在觀察,而中國正站在另一輪歷史轉折點上。未來的全球競爭不會因關稅、圍堵或科技制裁而停止,它將更取決於一個國家在技術突破、制度創新、人口調適與全球治理能力上的長期定力。中國能否讓自己的崛起走向更加穩健的階段,不只是中國的問題,更將深刻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形狀。
難以逆轉的「複合性下行旋渦」
近十年來,中國經濟雖仍以世界第二大體量運行,但其所面臨的壓力,已不再是典型的新興市場波動,而逐漸演變成一場全面性的結構性衰退風險。這場危機的本質,不是單純的增速下滑,而是多重因素長期、深刻、互相強化的拖累,形成一種難以逆轉的「複合性下行旋渦」。
官方口徑仍強調「韌性足、潛力大、空間廣」,然而現實卻顯示,這三項優勢正在被消磨,甚至在某些領域已開始逆轉。
中國正同時承受人口急速老化、房地產泡沫破裂、消費信心萎縮、產能過剩加劇、科技受限、外需疲弱、地方財政崩緊、民企投資意願低迷、制度預期不穩等力量的同時壓迫,並且任何一股力量都足以成為經濟停滯的主因;如今這些風險卻疊加在同一個時間點爆發,使問題變得更具時代斷層感——彷彿中國經濟正在跨入一個不可逆的下限時代。
中國的矛盾,不再只是短期需求不足,而是結構性的供需錯配,疊加制度性的不確定,形成巨大且逐步固化的陰影。
人口老化加重需求端的硬萎縮
中國面臨的第一道巨大陰影,就是人口危機的急速化。這不僅是老齡化的問題,更是「少子化+老齡化+人口負增長」三者同時惡化、彼此疊加。2023 年起,中國進入人口負成長,這比官方原先預期整整提前十年。更嚴峻的是,年輕世代的生育意願下降至全球最低水平之一。
人口急速老化意味著整個社會的消費結構轉變、勞動力減少、國家財政負擔提高。原本仰賴人口紅利支撐的製造業與房地產市場,都開始面臨需求端的硬萎縮。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成長,是由龐大的年輕勞動力、低成本製造與人口紅利共同堆起的奇蹟,但如今這些基礎正在迅速瓦解。人口萎縮所帶來的消費力下降,會使企業在「成本上升、需求下降」的環境下難以擴張。這意味著投資意願降低、工資增幅放緩、財政壓力擴大,而社會活力也隨之減退。
在消費不足的情況下,中國製造業轉向以擴大產能作為主要成長方式,尤其在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板、風電設備等領域形成大規模產能浪潮。這種投資背後,是在需求不振時仍被迫追求 GDP 增速的政策壓力。
產能過剩會導致價格戰
然而產能過剩會導致價格戰,企業利潤被嚴重擠壓,最後只能依靠政府補貼或傾銷海外來維持生存。當全球市場也出現飽和時,產能過剩將反向拖累中國自身的企業財務,並引爆貿易摩擦。歐美已對中國新能源產業展開反傾銷調查,這預示著中國外需將面臨更大阻力。
中國過去依靠出口帶動經濟,但全球供應鏈正在重組,「去中化」趨勢明顯。美國與歐洲紛紛對半導體、人工智慧、高科技關鍵設備實施限制,使中國的科技產業被迫停在價值鏈的中段。中美科技對抗,使中國難以獲得先進晶片與晶片製造設備,連帶影響 AI、高端製造與高附加價值產業的整體競爭力。
尤其半導體、電腦伺服器、AI 訓練、精密儀器的供應鏈中,缺乏先進晶片會形成天花板效應,使產業升級被迫放緩甚至倒退。外需疲弱與科技受阻,使出口不再能充當穩定的成長引擎。
地方財政困局絀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中國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LGFV)負債規模已逼近 9 兆美元,這是一個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黑洞。隨著房地產下行、土地財政銷售萎縮,地方政府收入銳減,但社會福利支出、基礎建設、教育醫療等基本開支卻無法減少。
債務壓力使地方政府對企業與民營經濟產生更強的攤派與稅收衝動,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亂罰款、亂攤派、亂收費」現象,使企業生存困難度加倍。地方財政惡化不但削弱政府投資能力,也直接影響營商環境與市場信心。
中國民營企業在經濟中過去曾占六成以上的投資動能,但近年因政治路線強調「強國企、弱民企」、「黨領導一切」,使企業感受到制度預期的不確定。中共反壟斷與平台整治曾重創科技巨頭,也讓民企普遍擔心政治風向突變。
民企不敢擴張、不敢加碼投資、不敢舉債,不是因為不看好市場,而是害怕政策風險。這種不確定性比經濟風險更可怕,因為它會使資本凍結、創新減速、青年創業意願全面下跌。制度風險成為壓住中國經濟活力的最大隱性力量。
青年失業率曾高達 21%,官方隨後直接停止公布數據,這使外界更加擔憂。大量畢業生找不到高薪工作,只能從事低端服務業或回家啃老。中國年輕世代開始流行「躺平」、「擺爛」、「不買房、不結婚、不努力」的心態,反映出對未來缺乏期待。
社會活力一旦下降,國家的長期創新與消費能力也會同步下跌。青年失業不是短期現象,而是經濟重組、科技轉型、產業升級不完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後果。
中國經濟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而是「政策驅動型經濟」。一旦政策方向擺動,整個市場環境便會迅速改變。因此制度預期的穩定性至關重要,但近年政策風向變化過快過急,使企業難以建立中長期規劃。
面臨最艱難的十年
從「共同富裕」、「反壟斷」、「平台整治」、「房市去槓桿」、「雙循環」到「新質生產力」,政策標語常常在短期內快速更迭。企業難以判斷真正的風向,只能選擇保守經營。政治的不確定性,使經濟失去活力,也使外資縮手。
中國如今所面臨的危機,已不只是短期的經濟調整,而是關乎下一個三十年的發展路線。若無法成功轉型,中國將陷入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低端製造競爭力下降,高端製造無法突破,內需不振、外需受阻,社會老化、創新不足、制度封閉,使國家停滯在中等收入階段。
中國若要避免衰退,就需要進行更深刻的改革,包括提升民營經濟信心、減輕政府干預、改善財政結構、推動真正的社會安全網改革、鬆綁創新限制、改善消費者預期。然而這些改革在政治結構下都存在巨大阻力,這才是中國經濟前景最不確定之處。
中國經濟正一步步進入「增速下降、風險累積、體制僵固、人口萎縮、信心消退」的時代。這不是崩潰,而是一種更深沉、更長期的衰退曲線,緩慢、但是難以逆轉。未來中國仍將保有龐大的產能與市場,但其動能、效率、創新、信心與活力正在快速下降。這場經濟陰影的本質是一場錯過改革窗口後的結構性退潮,而中國正在面對它最艱難的十年。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