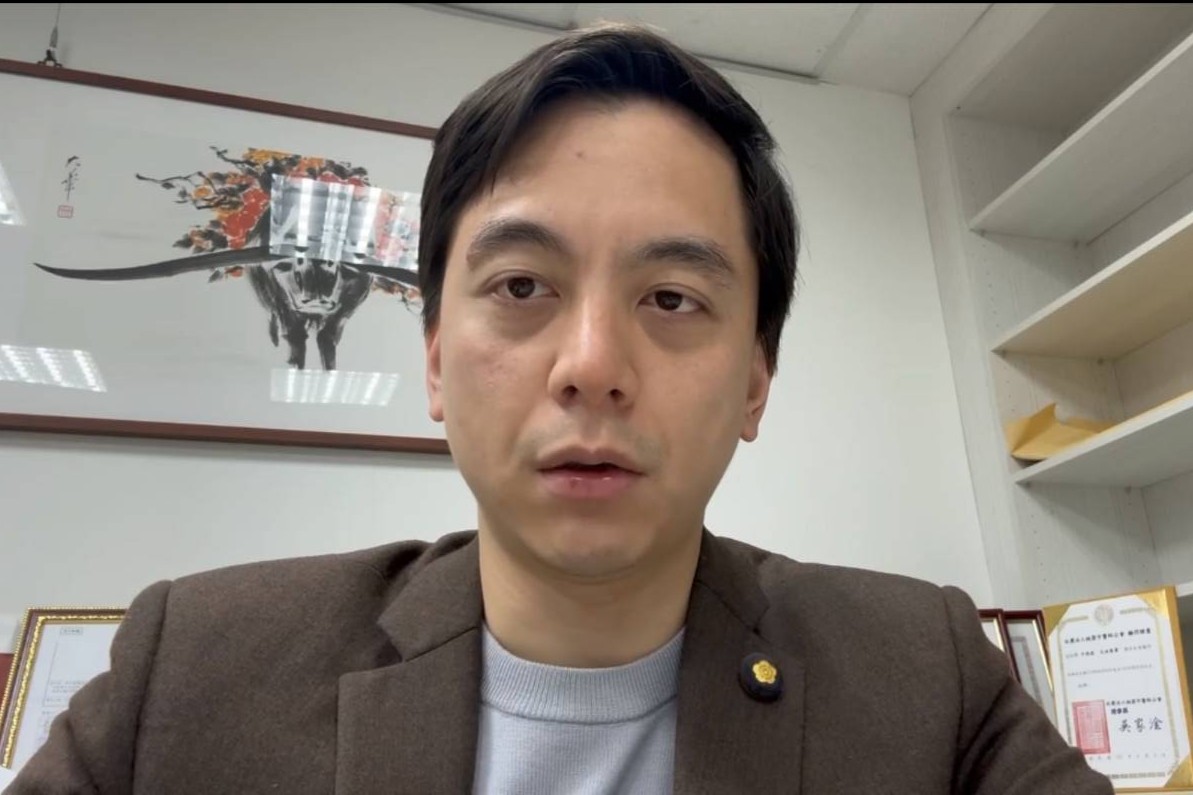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MSC)的核心雖涵蓋全球安全議題,但美歐關係是其中的關鍵焦點。當歐洲官員齊聚今年的峰會時,他們仍震驚於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長達90分鐘的通話內容,以及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布魯塞爾的談話。對立陶宛前外長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來說,赫格塞斯最令人不寒而慄的一句話是:「現實因素將使美國無法再擔任歐洲的安全保障者。」換句話說,美國不再是歐洲的後盾。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評論版主編戴特默(Jamie Dettmer)以《這是北約的末日嗎?》(Is this the end of NATO?)為題撰文指出,美國總統川普長期以來是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崇拜者。但如果英國這位象徵性的戰時領袖親臨2025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會作何感想?87年前,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離開這座巴伐利亞城市時,邱吉爾對他發出的譴責:「你面對戰爭與恥辱的選擇。你選擇了恥辱,但你終將面對戰爭。」張伯倫手持一紙對納粹政權而言最終毫無意義的協議。。
戴特默文中指出,如果邱吉爾看到川普如今推動結束烏克蘭戰爭的計劃,而基輔及其歐洲盟友擔憂這將有利於莫斯科,甚至可能埋下未來更大規模戰爭的種子,他是否也會做出類似的評價?「綏靖」(appeasement)一詞如今在歐洲頻繁出現,對於歷史敏感度較高的人來說,當前局勢讓人不禁聯想到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像藍斯柏吉斯這樣的觀察者感受到,一個時代的結束或許已經來臨。他表示:「這可能標誌著北約的黃昏,特別是當華府即將宣布從歐洲撤回2萬名美軍。」
當藍斯柏吉斯在慕尼黑接受Politico訪問時,赫格塞斯正在華沙發表演說,暗示美軍即將撤離,並警告本就焦慮不安的歐洲國家:「現在是時候投資自身安全了,因為你們不能再假設美國在這裡的軍事存在會持續下去。」
戴特默文章指出,川普政府的「震撼與恐嚇」(shock-and-awe)策略不僅在美國國內引發混亂,在歐洲也是如此。這種策略的目的顯然是讓對手與批評者措手不及,無暇應對與重新調整。參與峰會的美國國會議員試圖安撫歐洲盟友的憂慮,但收效甚微。其中,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威克(Roger Wicker)說,赫格塞斯在布魯塞爾的發言是「新手錯誤」:「我不知道那篇演講稿是誰寫的,但它的內容簡直像卡爾森(Tucker Carlson,編按親俄、反北約的右翼媒體人)的觀點。他是個蠢貨。」威克試圖緩和歐洲的擔憂,保證川普身邊仍有許多「嚴肅的專業人士」。
威克補充說,赫格塞斯已對部分強硬言論作出修正,但他仍未收回「美國將不再是歐洲的安全保障」的說法,而這正是讓歐洲最為不安的一點,因為這等同於否定北約第五條共同防禦的承諾。這句話,再加上另一句「別搞錯了,川普總統不會讓山姆大叔(Uncle Sam)變成冤大頭(Uncle Sucker)。」讓歐洲各國更加不安。
文章提到,英國智庫皇家戰略研究所(Chatham House)專家賈爾斯(Keir Giles)說:「川普直接與普丁接觸,再加上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告訴歐洲盟友,美國在談判開始前就已主動接受部分俄羅斯的核心要求,這對烏克蘭和歐洲的未來來說,都是雙重打擊。」賈爾斯進一步表示:「接受侵略者保留已佔領的領土,換取和平請願,這與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再相似不過了。如果川普拿著一張紙,宣布普丁保證不會再有進一步的領土野心,那歷史將真正重演。」
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在慕尼黑的演講聚焦於批評歐洲內部的民主問題,未能緩解歐洲的不安,反而進一步加深疑慮,甚至連親北約的美國人士也對此感到不滿。范斯的發言冷場不斷,除了零星的掌聲與幾個禮貌性點頭外,整場演說氣氛冷淡。當范斯談及移民問題,聲稱「我最擔心歐洲的威脅並非來自俄羅斯或中國,而是內部威脅」時,場內更是反應冷漠。
前美國外交官、學者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說:「試想,一個在2020年與煽動國會暴動者同台競選的人(范斯),如今竟然來到歐洲,對歐洲民主指指點點。」麥克福爾批評,范斯完全忽視了當前的關鍵問題—烏克蘭戰爭。「他本可以利用這場演講來澄清美國的談判立場,但他選擇不談。這場演說顯然是為美國國內選民準備的,而不是講給慕尼黑峰會代表聽的。」
3年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北約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存在意義。冷戰結束後,北約曾一度面臨如何確立自身存在意義的挑戰。但在這場峰會的第一天,歐洲官員普遍感受到內部正在出現裂痕。當然,川普第一個任期內的北約峰會同樣充滿美歐緊張關係,但當時美國的國安團隊仍會努力平衡局勢。如今,一切變得更加嚴峻,因為「山姆大叔」可能真的要抽身而去。
前德國外交官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說:「歐洲還能依靠誰?或許,只能靠自己。」他指出:「也許歐洲需要被電擊一下,讓我們意識到必須更具自主性,承擔更多責任。」伊辛格認為,歐洲各國領袖也要為當前困境負責。他們早被警告過,知道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可能會帶來什麼,但卻行動遲緩,未能大幅增加國防支出,未能真正承擔跨大西洋安全的責任。
立陶宛國安顧問布德里斯(Kęstutis Budrys)也承認歐洲應該更早行動:「我們確實遲了。我們必須加快步伐,展現出我們真正擁有防禦能力,並已做好作戰準備。」但他仍抱持希望:「我們提到1938年,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歷史教訓,並且正在努力避免重蹈覆轍。」
戴特默最後提到,一位歐盟高級外交官則悲觀地表示:「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位想摧毀歐洲的俄羅斯總統,以及一位同樣想摧毀歐洲的美國總統。」他沉痛地說:「跨大西洋聯盟已經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