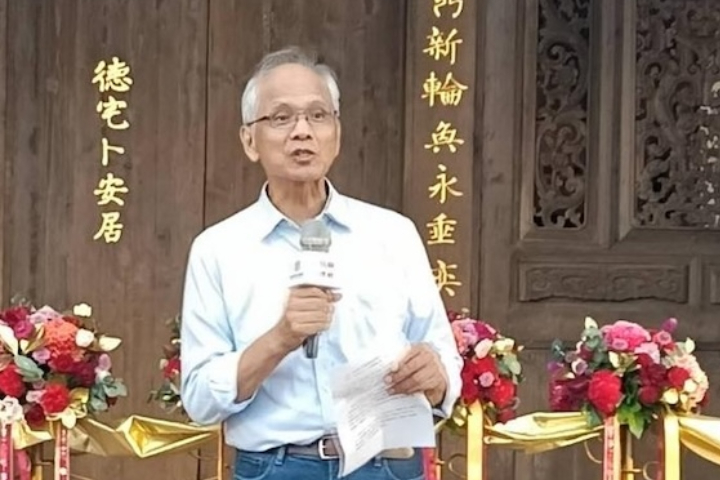翁履中/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近期,執政黨接連遭遇兩項重大挑戰:第一輪罷免投票慘敗,對美關稅談判亦告失利。臺灣不僅要面對疊加於現有稅率之上的20%對等關稅——高於日韓、甚至部分東南亞國家——原本規劃的美國過境行程也傳出因華府顧慮北京反應而取消。即使是力挺執政黨的選民,也難否認,如今的臺美關係已不復蔡英文時期那般,足以成為外交政績的亮點。
同樣是民進黨執政,落差卻顯而易見。蔡英文總統對國際事務的熟稔,加上拜登政府傳統建制派的全球主義框架,配合當時駐美代表蕭美琴的協調,成功將「民主價值+盟友關係」的敘事與美中緊張結合,使臺灣的戰略地位在華府持續被凸顯。相較之下,賴清德政府對國際事務的理解有限,對蔡英文外交團隊的延續安排缺乏信任,連副總統蕭美琴在外交決策中能發揮的空間也遠不如外界預期。姑且不論蕭美琴是否與民主黨淵源較深,但她對美國政治生態的理解,顯然未被納入當前決策核心。
若以考試作比喻,蔡英文時期的臺美關係,像自然組考生拿到社會組數學題,雖然題型不熟,但憑基本功就可拿到不錯成績;賴清德政府面對的川普外交,則像社會組學生突然接到奧林匹亞數學試卷,不僅難度陡升,連解題邏輯都完全陌生,落差自然一目了然。
更複雜的是,川普回鍋後的美國,已從價值驅動轉為「美國利益中心論」。在川普眼中,臺灣的重要性不過「筆尖大小」。然而,比外交成績下滑更嚴重的,是賴政府對批評與建言的態度。前川普顧問惠頓在〈臺灣如何失去川普〉一文中批評臺北策略失當,雖有誇張之處,但包括葛來儀在內的多位華府涉臺專家都認為文章反映部分真實情況。
遺憾的是,執政黨的第一反應不是檢討,而是質疑惠頓「狹怨報復」,甚至將各方建言描繪成「疑美論」的操作,歸咎於北京以及臺灣內部有親中勢力。外交上,不是不能回擊批評,但差別在於是讓對方理虧,還是讓對方積怨。對方若在川普圈子仍具影響力,臺灣的這種反應,對臺灣真的有利?
回顧過去,蔡英文與馬英九兩位前總統雖分屬不同路線,但在處理對美關係上的某些時刻,都展現了格局與務實。2019年,蔡政府面對臺灣未被納入美國印太經濟架構,沒有急著公開抱怨或動員輿論,而是低調啟動跨部門、多層次溝通,由外交部、經濟部與駐美代表處分頭與國會友臺派、商會及白宮經濟團隊接觸,最終為後來的「台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奠定基礎。馬政府在2008年美方因為美牛進口爭議暫停臺美TIFA會談,在國內輿論高度反彈的壓力下,同樣避免與美方和國內批評聲音在媒體上硬碰硬,透過與美國國會農業委員會、州政府以及美國肉品協會的分層協商,逐步拆解爭議,以配套食品安全措施換取美方重啟會談。兩位總統在這些事件中都面對到國內民意的壓力,但他們的處理重點並非消除質疑、壓制反對聲音,而是務實地解決面對美國的挑戰,確保臺美互動穩定。
維持良好關係,務實解決爭議是臺美外交的重中之重。當前關稅談判的困境正是例證。當川普積極尋求與中國交易時,北京手上的籌碼——市場規模、購買承諾、地緣影響力——遠勝臺北。臺灣無論付出多少,恐怕都難在川普眼中比中國更有談判價值。但若川普身邊有對臺灣友善的聲音,例如黃仁勳在晶片關稅問題上的發聲,仍能為臺灣爭取豁免或緩衝空間。川普時代的對美關係,比的不是價值同盟,而是人脈布局與利益交換,這些外交眉角,臺灣駐外人員甚至副總統蕭美琴都心知肚明,但顯然,建言沒有被採納。
在臺灣遇到對美關係挫敗之際,本應看到政府積極務實地處理,爭取修補空間,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執政黨將重點放在貶低來自美國的發言,抹紅國內批評聲音,甚至繼續力推第二輪大罷免,試圖用國內政治操作轉移來自美國的壓力,以及臺美關係不如過去的批判。持平而論,當前臺美關係不如過去,並非因為臺灣不夠親美,而是因為川普政府對臺灣的認知,導致臺美關係出現侷限。然而,即使如此,臺灣也不是完全沒有被看上眼的價值,問題是如何將臺灣的聲音,透過務實而靈活的外交手腕傳遞到川普身邊!領導人是否願意尊重專業、重視建言,並在錯誤中反省與修正才是重點。
說真的,惠頓說的不盡正確,因為臺灣不是失去川普,而是失去了方向!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