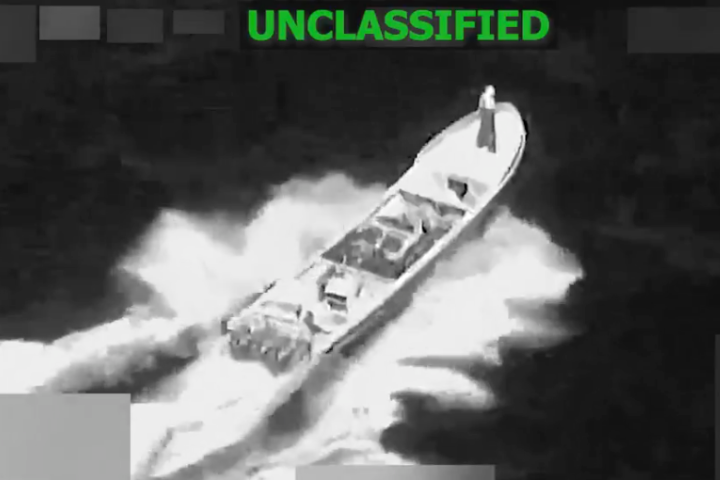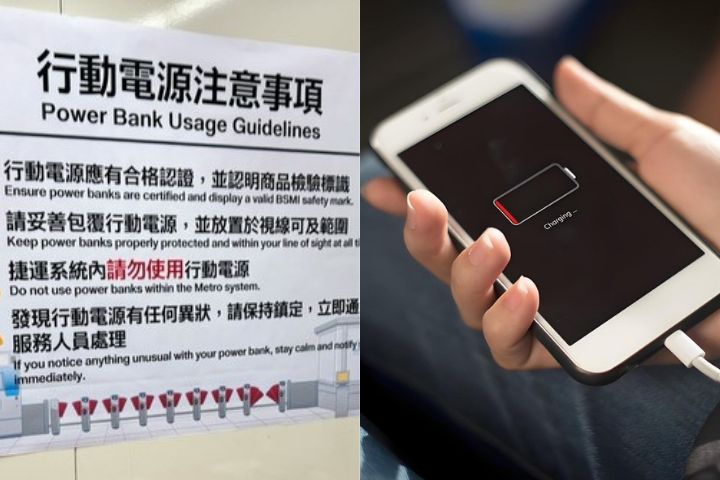黃靖麟/國立大學副教授
2025年9月,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滾滾泥流淹沒光復鄉,這不僅是一場天災,更暴露了深層的政府治理危機。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政治對立,在勘災現場上演激烈爭執,導致救災指揮系統失能,形成致命的領導真空。儘管科學預警早已存在,但是撤離指令的混亂與「垂直避難」策略的慘痛失敗,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
在政府失靈的同時,數以萬計被譽為「鏟子超人」的公民,自發性地湧入災區,填補了國家權力留下的空間。他們的行動,為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理論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台灣案例。
鏟子超人:典型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理論,旨在闡釋人際網路中所蘊含的無形力量。其建立在信任 、規範 與網絡 等三大範疇上。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視其為一種個人可動員的資源以鞏固社會地位。但是,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的觀點,更能解釋光復鄉的現象。普特南將社會資本視為促進集體利益的公共財,並做出下面二種關鍵區分:
1. 凝聚型社會資本 : 如同社會的「強力膠」,強化同質群體(如家庭、宗親)的內部連結。
2. 橋接型社會資本 : 如同社會的「潤滑劑」,建立不同群體的聯繫,讓陌生人得以合作。
「鏟子超人」現象,正是橋接型社會資本的極致展現。
政府辜負人民時仰賴公民互助
當政府指揮失序時,一個由公民自發形成的臨時指揮系統,在光復車站悄然成形。成千上萬的志工,來自不同背景、互不相識,卻因一個共同目標而集結。他們憑藉著高度的「普遍信任」,相信自己的付出有其意義,也相信現場的陌生人會彼此協力。光復鄉自發性的公民行動,匯集了台灣社會的縮影:年輕學生、退休人士、專業人士,甚至是旅居台灣的外籍人士。他們的動機,完美印證了「互惠規範」的存在。一位志工接受媒體訪問時坦言,之所以前來是為了回報過去家人曾受花蓮鄉親幫助的恩情;另一群前壘球隊員則是為了幫助昔日教練的部落。這些行動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慈善,成為一種深刻的社會契約實踐:當正式制度辜負人民時,公民之間的信任與互助網絡,便成為社會最有力的防線。
光復鄉的公民響應並非偶然,而是台灣「公民社會」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自1999年的921大地震後,台灣便贏得了「志工島」的美名,公民自主救災的文化腳本已深植人心。這股能量不僅在災難時爆發,更根植於全台無數「社區營造」 的日常實踐中。
「鏟子超人」的出現,意味著台灣公民社會的成熟。它已從威權時代的附庸,成長為一股能與國家並行,甚至在必要時取而代之的自主力量。這股力量為台灣的民主韌性帶來了希望,也對政府治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國家必須成為一個更值得信賴的夥伴,才能匹配其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志工們用行動證明,當國家失能時,人民有能力自我治理,這正是對主權在民最深刻的詮釋。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