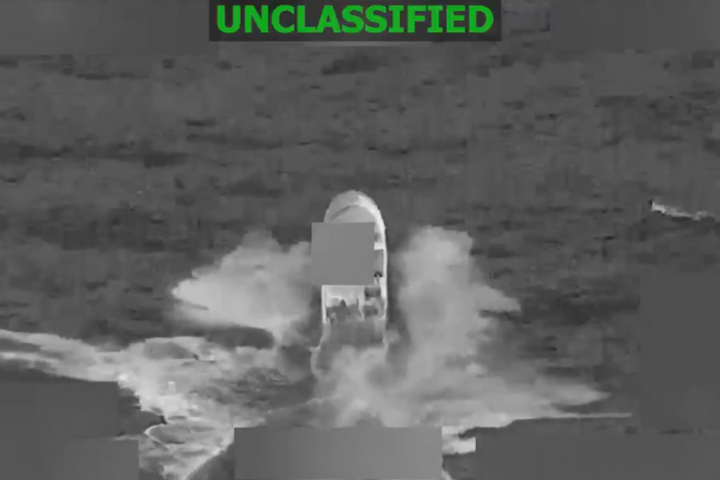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在當今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戰略競爭日益激烈之際,歷史經驗提供了一面珍貴的借鏡。1980年代,美國曾面臨日本的強勢經濟挑戰,當時日本看似即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霸主。然而,經過一系列戰略調整,美國最終在關鍵領域成功壓制了日本的競爭勢頭,這過程中的策略與手段,對於理解當前美中競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歷史重演?從美日競爭到美中對抗
1980年代,日本經濟實力急劇擴張,在汽車、電子產品和半導體等多個重要產業領域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當時,許多專家學者甚至預測日本將很快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當時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於1979年出版的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產生了深遠影響,書中警示日本在產業效率與社會治理上的優勢,強化了「日本第一」的論調,在美國引起廣泛憂慮與深刻反思。
當時日本的競爭優勢建立在獨特的產業政策、勤奮的勞動力以及卓越的製造技術基礎上。四十年後的今天,美國面對的中國大陸挑戰規模更大,範圍更廣,但基本性質相似,一個新興強權試圖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奪取主導地位。
與當年的日本不同,中國大陸不僅是一個製造業大國,更是擁有核武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其政治體制和經濟規模都使當前的競爭更加複雜。然而,美國在應對日本挑戰時採用的戰略組合,仍為當前局勢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框架。
經濟制衡:從戰略壓制到「失落三十年」
美國在應對日本經濟挑戰時,採取了一系列主動且強硬的戰略壓制措施。1985年9月簽署的廣場協議是其核心舉措,美國透過多邊合作迫使日圓大幅升值,直接削弱了日本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這一行動是美國為削弱競爭對手、維護自身經濟霸權而發起的戰略性金融戰。
在廣場協議之後,美國更通過一系列雙邊談判,如日美結構性障礙協議,直接干預日本國內經濟政策,要求其改變經濟結構、開放市場。同時,美國頻繁使用反傾銷調查、301條款等單邊主義工具,對日本的半導體、汽車等核心產業課以重稅和出口限制。
這些外部壓力與日本國內原有的資產泡沫問題產生共振,最終成為刺破日本經濟泡沫的直接導火索。隨後,在美國戰略性打壓所製造的危機下,日本原有的結構性弊端全面暴露並加劇,最終導致了「失落的三十年」。日本的長期停滯,是美國外部戰略打壓與日本內部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結果。
科技創新:美國的核心反擊策略
面對日本的競爭,美國認識到單純的防禦性措施不足以確保長期優勢。因此,美國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大力推動科技創新,特別是加強在半導體、計算機軟體和網路技術等新興領域的研發投入。這種戰略轉向最終為美國在1990年代主導資訊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礎。
美國政府與民間企業合作,建立了有利於創新的生態系統。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在推動關鍵技術突破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最初為軍事目的開發的技術後來都轉為民用,促進了整個科技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美國的風險投資行業迅速成長,為新創企業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
在高等教育領域,美國加強了與科技產業的合作,培養了大量工程師和科學家。美國大學的研究實驗室成為技術創新的重要源泉,許多突破性技術都源自學術機構。這種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模式,使美國在質量上超越了日本的技術能力。
1990年代,美國成功地從工業經濟轉型為知識經濟,而日本則未能及時完成這一轉變。美國在軟體、網際網路和數位服務等新興領域建立了絕對優勢,這些領域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日本擅長的硬體製造業。
制度優勢:靈活性與適應性
美國在與日本競爭過程中所展現的制度靈活性,是其最終取得優勢的關鍵因素之一。與日本僵化的經濟結構相比,美國的市場經濟更具適應性和創新能力。美國企業能夠快速調整策略,重新配置資源,應對市場變化,這種特點在科技快速迭代的時代尤其重要。
美國的勞動市場流動性較高,資本配置效率也更勝一籌。當新興產業出現時,美國能夠迅速將人才和資金引導至這些領域,而日本則受制於終身僱用制等傳統,難以實現類似的資源重新配置。這種結構性差異在1990年代變得更加明顯。
美國的另一個優勢在於其開放性,能夠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前往美國,為美國的科技創新注入新的活力。相比之下,日本的封閉性限制了其獲取全球人才的能力。
金融體系的差異也是重要因素。美國的資本市場更願意支持高風險、高回報的創新項目,而日本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則偏向保守,更傾向於支持傳統產業。這種差異使美國在新興科技領域擁有明顯優勢。
對當前美中競爭的啟示
從美國戰勝日本的歷史經驗來看,當前的美中競爭可能會呈現幾個關鍵特點。首先,經濟與技術的競爭將是核心領域,軍事對抗未必會成為主流。美國很可能繼續利用其在金融、科技和國際規則制定方面的優勢來制衡大陸的崛起。
其次,創新能力將比生產能力更為重要。當年美國通過開創資訊科技新範式而取得對日優勢,今天則需要在新一代技術如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生物科技領域建立領先地位。大陸雖然在製造規模上具有優勢,但在原始創新方面仍面臨挑戰。
第三,聯盟網絡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在與日本競爭時,美國積極利用國際多邊機構和盟友體系施加壓力。在當前環境下,美國同樣試圖通過與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合作,共同應對大陸的挑戰。
最後,內部活力將是決定競爭結果的關鍵因素。美國當年能夠戰勝日本,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社會的開放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今天,美國需要解決內部分裂、政治極化等問題,才能有效應對來自大陸的挑戰。
從1980年代美國為消除「日本第一」憂慮而發動經濟金融壓制,到最終促成日本陷入「失落的三十年」,這段歷史提供了真實的霸權競爭範本。它顯示守成霸權完全願意運用其綜合優勢,主動出擊以系統性削弱競爭對手。
傅高義《日本第一》從預言到現實的落差,見證了這一博弈過程。美國當前對華的關稅戰、科技封鎖與聯盟遏制,與當年對日策略一脈相承,且規模與強度更甚。歷史表明,大國競爭的結局不僅取決於挑戰者的實力,更取決於守成霸權的戰略意圖與遏制能力。
中國大陸需從日本經驗中汲取的,不僅是產業升級之道,更是應對美國系統性壓制的深刻教訓。這場競爭的結果,將決定兩國命運,並塑造21世紀的全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