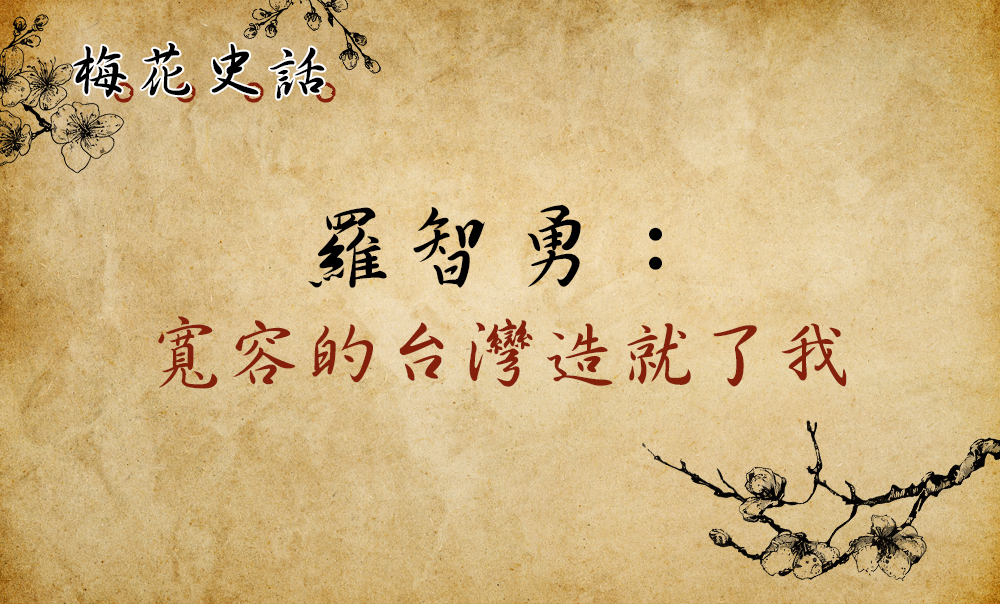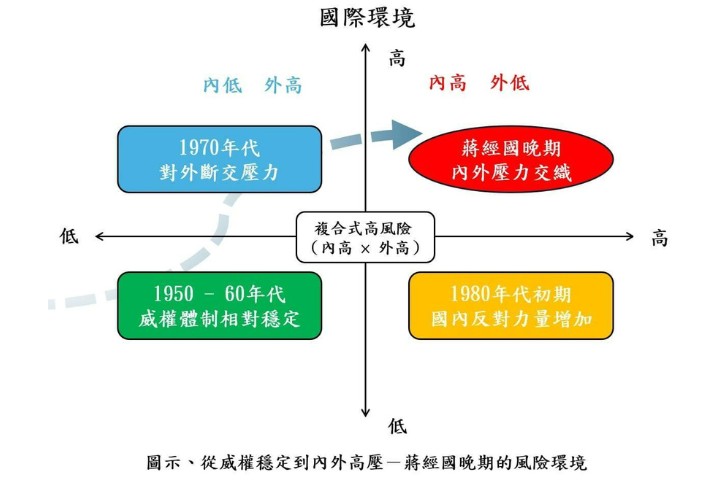(編者按:羅智勇,出生在花蓮,其父母在1955年大陳島撤退來台。現鑫波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其弟為現任國民黨立法委員羅智強。)
我們是台灣新移民
我的父親1938年生,母親1945年生,他們在1955年大陳島的大撤退中,跟隨他們各自的父母到達基隆,再按照政府的分派舉家搬到了花蓮,就此在台安居。1949年國民黨軍隊到大陳島時,徵用過我家的房子,有趣的是,到了台灣之後,我們還遇到一位曾在我家住過的軍官。
聽父親說,大撤退的那天,因為祖父生病了,叔叔年紀又小,所以17歲的父親必須擔負起搬運的任務,但提著兩個行李箱的他卻在路途中被軍隊抓去當行李工。後來父親兩度找機會跑回家,但又都被抓回去。最後,父親搭美國第七艦隊來台灣,隔天清晨抵達基隆港。父親對大陳島的最後印象是當時第七艦隊船隻包圍了大陳島,海上全是船艦,天上全是飛機。應該說,祖父在大陳島的生活水準算富裕,但來台後就變得一無所有了,身為長子的父親十幾歲就幫著祖父母掙錢養家,一塊拉拔著家裡幾個弟妹長大,日子過得很清苦。
我們家三兄妹,我是大哥,還有弟弟羅志強,妹妹羅美娟,我們都在花蓮的大陳一村出生。我讀幼稚園之前,都講大陳話,但是父母會教我們講一些國語。青壯年在大陳新村基本沒有發展,大都出去打工了。為了謀生,父親也四處做工,曾參與興建中橫、蓋橋鋪路等,但經常會遇到工頭薪水發不出的情況。父親也當過義務制的兵,但為了讓生活安定,就回去當志願兵,勉強維持生活的開銷。最後父親應徵到基隆碼頭當工人,全家從大陳一村搬到基隆居住,一家人的生活才算就此安定下來。我母親繡花貼補家用,縫釘歌星衣服上的亮片,利潤還蠻好,後來她去台北批發,並組織鄰居一起做,有點家庭工廠的感覺,只是這種服飾早已經沒落了。我大學讀軍校,就是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
雖然在台灣長大,但我們不太會講台語,因此稍微有點被當地人排斥的感覺,但是上國中和高中後就沒這樣的問題了。父母都是大陳島人,我們的血液裡流的是大陳島的血,可以說是純種的大陳人。被問起是哪裡出生的,在台灣我會說花蓮出生的,在大陸我會說我也是浙江人,是中國人。
記憶闌珊的大陳一村
大陳一村位於花蓮市府前路旁,緊鄰花蓮榮民之家,是花蓮市區往七星潭、花蓮機場或中橫的必經之路,這是父母親來到台灣之後第一個落腳的地方。後來父母到了適婚年齡,便在祖父母與外祖父母的撮合下結婚。當時村裡時興這樣的婚姻,因為全村都是身無分文地來到台灣,為了減省婚嫁費用,大都憑藉雙方父母磋商後敲定。
父母新婚時,外祖父母挪了隔壁一間小房間給父母當新房,祖父則送了一個陶製的小瓦罐,讓母親炊飯用的,可是沒有睡的床,父親就向村裡表舅、表姑姨婆等借錢,湊了一千塊錢買張新床安家,然後去當時正開建的中橫公路當搬運工,每天辛苦地將山上的石塊挑運到山下,賺取微薄的工資養家,母親則在家縫補漁網貼補家用,不想幾個月下來,工頭將父親等幾個工人的工資捲走跑了,父親又改去當花蓮港的碼頭工人,總之,這一千塊錢,父親足足用了一年才還清。
村子搭建模式與一般眷村並無二致,都是木造的平房,一家挨著一家,雞犬相聞。隔音效果很不好,而大陳人的嗓門又很大,於是隔壁吵架、打小孩的聲音都聽得到。屋頂澆著厚厚的柏油以防漏水,但每一次颱風,屋頂就被掀掉一次。
對小孩子來說最興奮的是過年前夕的打年糕,大人們輪流打年糕,將年糕捏成各種形狀,而小孩子們則歡喜地圍在旁邊,拿起剛打出來的年糕直接放在嘴裡咬,很香很Q。到了吃鰻魚的季節,我們去市場買鰻魚,把它切開,把骨頭剔掉,對切,做成鰻魚乾,或者加鈦白粉變成鰻魚麵。
破舊的矮房子,濃鬱的香味,外婆蒼老的臉……一幅幅圖景在記憶深處依然清晰。現今這個村內部分房舍已原地改建成鋼筋水泥的房子,但曲折的巷弄仍維持著兒時的景況。因為自小就遠離大陳新村,聯繫也不多,因此我對大陳同鄉並沒有太多印象。
時代在大踏步向前邁進
父母現住在新北市的泰山,母親還在佛堂裡當義工,幫助鄉里,幫助往生者念經,空閒時會找三五好友去逛街、打麻將,生活充實而悠閒。在我父母的認知裡,只有受教育才能改變命運,因此對我們的期望很簡單,就是好好讀書,找到好工作。而今時代已改變,對我而言,我比較在乎孩子對事務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我讓他們學樂器、武術和音樂,也經常和他們聊歷史故事。
我曾經做不動產的開發,2010年3月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主要從事大陸電子零件的進出口貿易,也會接些專案做規劃。比如按照客戶的要求設計一個購票系統,説明電影票的銷售者規劃一個語音買票系統等。也做居中協調的工作,比如大陸崑山的客戶想要尋找太陽能板的台灣廠商,我就幫助牽線搭橋。我去北京就是想看看有什麼專案可以與台灣的廠商合作。
全台灣每年都有100多項文學獎的角逐,很多基金會、媒體等機構都會舉辦各類獎項,吸引熱愛文學的民眾參與,充分體現了台灣的文化氛圍。有一些文壇上的朋友,在台灣出書也不掙錢,乾脆就參加各種文學獎貼補家用,畢竟這些獎項的獎金很可觀,有的甚至達到100萬新台幣。我曾經連續5年參加文學獎項。可以說,台灣中生代比較務實,他們比較不會去想國家、政治的概念,而是想著怎樣讓生活過得更好。我的價值觀和同輩沒什麼差異。我工作上的目標是開發客戶,得到客戶的信任,並與之和諧相處,生活上的目標是樂於和他人交往,最終的目標是無論在婚姻還是事業,我都能夠獨當一面。
這些年台灣社會被刻意去中國化,我覺得過多探討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問題是一種情緒化的表現。中國在歷史上就分分合合,但中華民族血濃於水的情結從來沒有改變過。可能我的孩子未來也會去對岸找工作,在那裡落地生根。
台灣與中國大陸,這從來不是一個問題。
(本文轉載自陳玲著《大陳記憶─兩岸新移民的悲歡》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