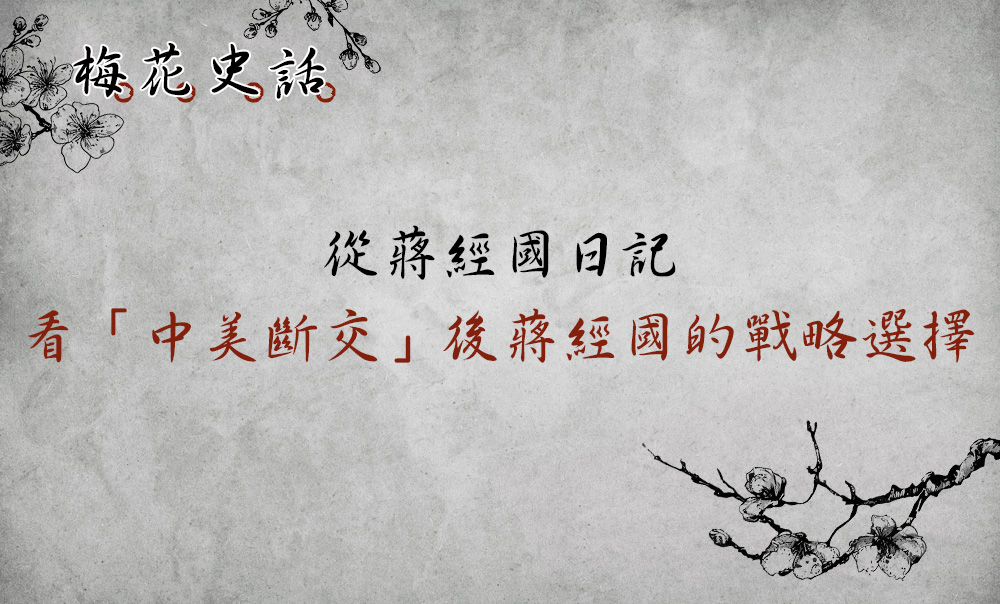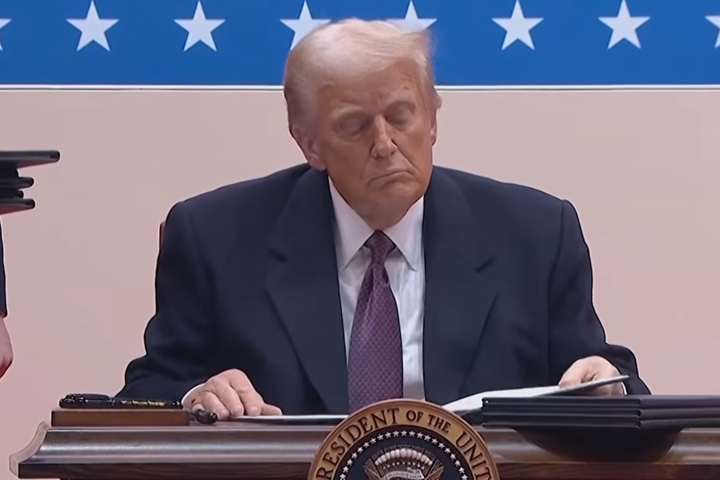美國前總統卡特過世,享壽100歲。在他任內,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廢止《中美協防條約》,美軍撤離台灣。今天在台灣五十多歲以上的台灣人對當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那段驚恐不安、風雨飄搖的日子,可能多少還有一些印象。 但是台灣挺了過來,依舊經濟繁榮、民主發展,這與當年主政的蔣經國當時的一些判斷與決策不無關係。本文試圖從後來公開的《蔣經國日記》一窺他在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下的心路歷程與決策思考。
雖然時任總統的蔣經國對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已有心理準備,但是當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於1978年12月16日凌晨2時,把早已服用安眠藥入睡的蔣經國從被窩裡挖起來,告知美國將在未來數小時內宣布與中共建交,根據蔣經國日記記載當時他「內心痛苦,身負重責只好理性處理,先安人心」。
早在1971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台北竟有預感兩國關係不穩,但是許多人不願面對。要不是尼克森受到「水門案」影響下台,美國與中國可能還會提早個幾年建交。當美國開始緊鑼密鼓積極洽談建交細節,蔣經國感受到巨大的壓力。
1978年底台北已經掌握到美國與中共建交已是箭在弦上,情報陸續傳回台北,蔣經國在11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批閱美國政府準備和共匪正式談判所謂正常化之綱領密件,其真實性似可信。美帝在此一文件中,充分表現出了無能無恥,有意向共匪做無條件投降,無人對於可能發生的各種變化,擬定應付的辦法。進來將以處理對美關係以及發展國防科學作為工作之重。」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對國民政府衝擊最大的正是斷交後如何與美國維繫交往,以及美國撤軍後台澎金馬的防衛問題。從後來與美國的談判在黨內的巨大壓力下,務實面對,委曲求全,努力達成美國與台灣非傳統的外交關係,實非易事,美台雙方也是絞盡腦汁。
衝擊更大是的沒有了美軍的協防,如何展現國防自主與防衛決心,以安定民心,更是一大挑戰,蔣經國後來投注大量資源在國防科技上自主研發,取得一定的成就,就是這種臥薪嘗膽的成果。
12月6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絕不與共匪妥協;二、絕不與蘇俄交往;三、絕不讓台灣獨立;四、絕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這時他已經對即將到來的「中美斷交」規劃整體的國際、兩岸與內政的大方向。
這裡補充一點,蔣經國當時已經預見美國將拋棄國民政府,但他決定不打蘇聯牌,不代表國民黨與蘇聯沒有私下接觸的管道。根據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教授的說法,胡佛檔案館所藏的宋鳳恩檔案,解密了當時台灣與蘇聯之間有一條不為人知的「柏林管道」,是由中央社派駐西柏林的主任宋鳳恩,與蘇聯國營通訊社塔斯社駐西柏林的主任巴赫穆夫接洽,雙方從1969年開始秘密接觸,期間超過一百次以上。 蘇聯方面曾經透過宋鳳恩向蔣氏政權提議,蘇聯願意派軍事顧問來台協助訓練、協助中華民國保住聯合國的代表權,希望台灣協助蘇聯蒐集中共情報作為交換。文化大革命期間雙方還密謀「南北夾擊」共同對付毛澤東。當美國與北京接觸後,台北擔心美國完全放棄台灣,於1972年下令宋鳳恩停止與蘇聯的接觸。同樣的邏輯可能出現在華盛頓與台北斷交這件事情上,可能蔣經國判斷:相較蘇聯,美國的支持對台灣來說還是十分重要也比較可信。但是從1980年代起,台灣也開始重視與東歐國家關係的發展,這就是後話了。
另外,當時蔣經國決定停止選舉,壓制黨內外民主聲浪,最後因為政權合法性因「中美斷交」遭到嚴重威脅,也做出調整,開始「本土化」與「民主化」保住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存續。
1978年12月27日晚間,時任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領代表團搭乘專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準備要與台北針對斷交後的台美關係展開談判。當晚機場外面民權東路與中山北路卻擠滿抗議人潮,群情沸騰,抗議民眾揮舞國旗、高舉布條、呼喊口號。美方代表團車隊出現後遭到民眾丟雞蛋、潑油漆的攻擊,場面幾乎失控。代表團決定縮短行程於29日離開,要求之後的談判改至華府進行。
蔣經國在日記中有這麼一段紀錄:「二十七日美國政府代表團深夜抵達台北時,受到示威群眾的嚴重干擾,乃是極為不利的意外事件,使我預布一盤有利的棋變得極為不利,群眾難以控制,深以為憾。代表團見了兩次,開了兩次會議,沒有協議,亦未破裂。」
這裡顯示蔣經國原本是想利用群眾幫助他完成「一盤有利的棋」,但是群眾失控,得罪了美國人。我們不知道原本小蔣構想的棋局為何,可能是希望利用政府與民眾的抗議對美國施加道德壓力。這似乎就高估了美國在國際現實主義下的道德標準了。另外,小蔣可能利用示威讓台北談判破局,等待美國國會開意議,讓國會介入,這也高估美國國會在外交政策的決策地位。這兩個誤判,讓台灣在後來談判中處於較為被動的地位。
總之,蔣經國在「中美斷交」的大變局中,蔣經國的戰略決策有堅持、有調整、也有誤判。在追悼卡特總統的過世的同時,撫今追昔,也要想想美國離開台灣後,台灣怎麼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