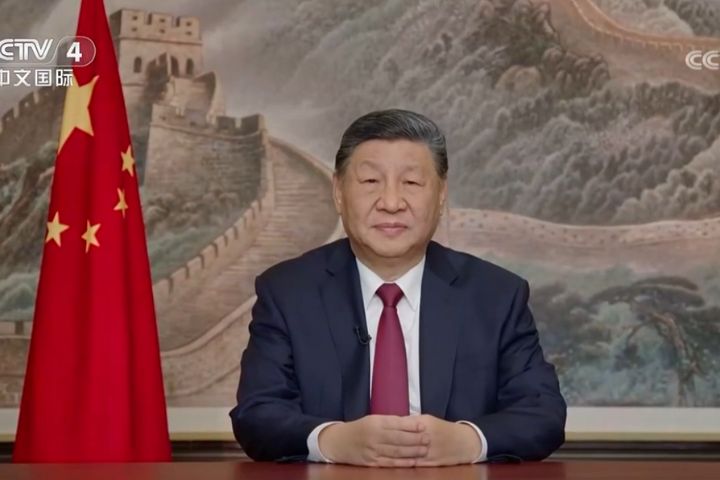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自從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起,西方就不時有學者與媒體提出中俄將形成反西方的新的地緣政治同盟。2004年中阿合作論壇成立、2023年伊朗加入上合組織,又有論者說這些趨勢印證已故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預測,即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將攜手對抗基督教文明,特別是伊朗在俄烏戰爭中援助俄國無人機,又強化了俄中伊攜手對抗西方的判斷。
新軸心集團有哪些,莫衷一是
關於朝鮮(北韓),本來在小布希反恐戰爭時被貼標「邪惡軸心」(Axis of Evil,與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後來朝鮮強硬退出中國主導的「朝核六方會談」,人們認為中朝關係疏遠。特別是俄烏戰爭中,平壤主動出兵俄羅斯庫爾斯克州(Kursk),對普京收復該州不無幫助,外界一度認為俄國成功將北韓從北京一側拉至莫斯科身邊。不料現在北京舉辦「九三閱兵」,金正恩在時隔6年後竟應允出席,於是外界又開始盛傳國際上將形成「中俄朝」三國軸心同盟。
至於向中方出售石油、給俄國無人機援助的伊朗,好像因為被川普B-2轟炸機的鑽地彈炸壞了核設施、炸死了革命衛隊司令,已經「斷手斷腳」,總統佩澤希齊揚 (Masoud Pezeshkian) 出席北京閱兵就稍受冷落,只能成為「混亂軸心」(Axis of Chaos)的跟班。
這些用二戰「同盟國vs.軸心國」比喻新冷戰中反對華府的概念,內容與成員一換再換,正說明了其本質也是一種「想像的混亂」(imagination of chaos),多半是反映鼓吹者們的猜測、心情與宣傳意圖,與當年「同盟vs.軸心」以及「北約vs.華約」的聯盟政治本質完全不同。
聯盟形成的條件
所謂聯盟政治,包括「同盟vs.軸心」以及「北約vs.華約」,法理與政治上是「攻守同盟」。亦即一國被擊,盟國相援。為何會形成聯盟?著名學者沃爾特(Stephen Walt)曾在《聯盟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攻守同盟」需符合數個條件:對手實力強大、對手地理鄰近、對手進攻手段與對手威脅明確。以此觀之,中俄朝伊等國的主要對手確實是美國,美國雖被認為可能處在「霸權下降」區間,實力仍首屈一指;雖然是否所有「西方陣營」都與美國同等反對四國則存在差異。
但從「地理鄰近」這個條件開始,中俄朝伊四國與美國/西方的關係就頗有差異。就美國具備全球進攻手段而言,對朝鮮與伊朗沒有地理「不鄰近」的問題,這也是北韓堅持發展長程戰略核武遏制美國的理由。但對中俄這樣具備足夠核子反擊能力的軍事超級大國而言,美國憑藉北約與西太平洋盟國才稱得上是鄰近威脅。事實上,美國作為「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反而無時無刻不在構思如何挑撥中俄這一組陸地邊界最長、過去領土糾紛眾多的陸權大國。川普與包括季辛吉等部分美國人士構思「反向季辛吉」(Kissinger reverse)戰略,其實普京總統知之甚明,也樂於「接球」。
美國沒有促成俄中結盟的理由
這也正好說明兩件事:第一、川普一再延遲俄烏談判期限,還冒北約盟國之不諱,在阿拉斯加舉行十年來首次美俄峰會;如果能藉此平息烏戰,就可冷卻歐洲緊張、拉開中俄,專著印太戰略。所以雖然美國公眾仍以俄國為對手,至少對川普團隊來講,莫斯科最多威脅歐洲盟國,對美國不構成首要威脅,沒有必要把它推向敵對聯盟。
第二、美方雖多次指控中方購買廉價俄國石油,又出售軍民兩用物資給普京政權,但至今官方認為「尚無直接證據證明俄國直接購買中國致命武器」的證據,最多只是「透過間接管道」或涉嫌交易零件。至於石油貿易,印度與中國都是廉價俄國產品的受益者。川普雖然加諸莫迪 (Narendra Modi) 50%關稅,但這主要是針對印方不開放有關市場,與中印購買普京石油關係較小。由此可知,中國對普京從事俄烏戰爭的資助,遠比出兵的朝鮮與直接提供成品的伊朗要隱晦得多。外界也頻傳莫斯科對「歷史最好時期」的中俄關係迭有怨言。這說明其實俄中雙方認為「結伴不結盟」才符合彼此利益,美國也因此有打「俄國牌」的空間。
聯盟政治亦非中國外交傳統
除了西方的聯盟理論外,還有一點能排除中俄朝伊「軸心」同盟。那就是中國外交傳統中的「中國中心」特色。這一從古代「天下觀」而來的「東西南北、中國居中」態度,使得中國除非面對敵手聲勢弱小,聯合回紇抗安祿山或聯合金朝以攻遼,或者「一邊倒」,否則強勢情況下「霸主的盟會」,更常像是自組社交網絡的盛會,而非西方多邊契約式的同盟。
也就是說,廣結善緣、羈縻分治(統一戰線)是中國外交的傳統;聯盟實是異例,不得已而為之。一帶一路、上合組織、金磚集團、全球南方與中俄朝伊作為「軸心盟國」,實在相去甚遠。
川金可能再會、北韓不會參加軸心
總之,所謂中、俄形成「軸心國」,實屬對兩國之厭惡的情感投射,並期待美國直接「捲入」(be entangled)其他受中俄脅迫國家的衝突,承擔「同盟責任」。至於中俄朝伊軸心,更是脫離現實。莫忘川普還期待再敘川金峰會,贏得諾獎;歷代金氏君主堅持朝鮮「主體思想」,也曾數度警惕黨內,不可過度期待中朝關係。金正恩前往北京,不過是包括韓國、巴西等周邊、全球南方等眾多收到邀請的國家之一,本來就可以選擇派誰出席。金氏出席,北京豈有為改善與李在明關係而不接待的理由?金正恩稍與北京靠近,說不定是川金下一輪互動的前奏?
最後,從川普政府「要地位至上不要霸權責任」(primacy but hegemonic responsibility) 的總方針而論,期待分化俄中、朝中尚嫌不足,怎能期待他自己去建構一個「軸心集團」,然後承擔「同盟國」的參戰責任?從任何方面看,就算有美中「新冷戰」,所謂「西方民主同盟vs.中俄朝(伊)軸心」,純屬臆想。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