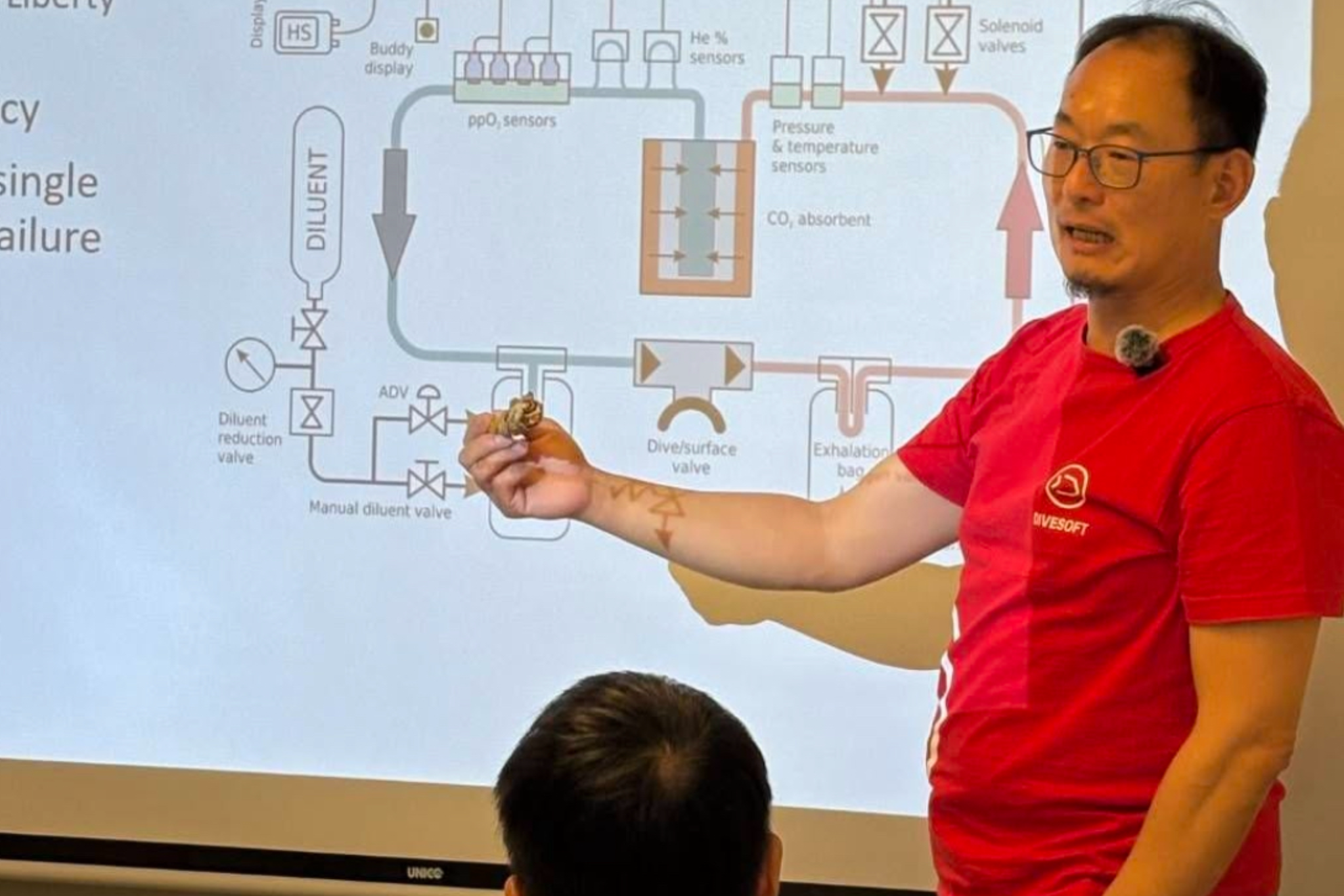陳熊赴滬「參謀旅行」之時間是在1937年的8月16日,讀者諸君一定以為我搞錯時間了,一點都沒弄錯,熊式輝與陳誠確是在8月16日到的上海,那時我軍雖已與倭寇接戰。但值得注意的一點,蔣先生命陳熊二人去上海作參謀旅行,雖然我軍與倭寇已經交戰三天多,但國民政府其實一直未對日宣戰,中國對日本宣戰還是在珍珠港事變,亦即滬戰爆發後四年的事了,中日之間持續四年間是處於一種不宣而戰的弔詭狀態之下。這種不宣而戰的狀態,就某種意義上而言,可說是為中倭關係「留白」,這種「留白」很可能是蔣先生在1937年8月的那個時間點上,為中倭關係一旦逆轉,由戰轉和,作的一種「預留伏筆」巧妙安排。可悲的是,倭寇的獸性本質怎麼可能懸崖勒馬及時悔悟呢?
陳誠在他的「六十自述」一書中,是這麼交代1937年8月16號的那次上海參謀之旅的經過的:「十六日,與熊主任天翼(式輝),赴上海晤張總司令治中。治中主一面著重宣傳,一面分軍為左右翼,進擊留滬之敵人。余認為非計之得。當增兵改攻匯山碼頭,向敵中央突破,截成兩段。然後向兩方掃蕩,使敵在上海無立足地。後未依照預定計畫,予以殲滅,致受沿江登陸之敵夾攻,殊為遺憾。八月十八日,與天翼同車返京,途中磋商如何覆命?余以介公天資卓越,請各就所見,分別建議,以供採擇」。
在過去,蔣介石對外,尤其是對倭寇,很多情況下是採取「隱忍」立場。1928年5月蔣先生率領北伐軍在濟南遭逢日軍突襲的記憶,是他畢生難忘的。倭寇竟然在中國的土地上,武裝挑釁,槍砲齊發,致使這支號稱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革命隊伍成軍以來,第一次遭遇到外國軍隊的襲擊(而且是毫無預警的突然攻擊,偷襲,十分符合倭寇賊頭賊腦的本性),無異敵國兩造之間已進入戰爭狀態。濟南慘案傷亡之慘重令人不忍卒睹,蔣介石眼界之中,濟南事變這等慘事,蔣某人皆可「唾面自乾」,而今,淞滬會戰固然規模較諸濟南慘案不知嚴重千萬倍,蔣先生雖然下令誓死抵抗,絕不忍受「唾面自乾」的奇恥大辱!但其實倭寇只要適度轉圜,適度給予國民政府該有的「薄面」,未嘗不會有戲劇性的和平結局,一如1932年的中倭淞滬軍事衝突,彼此軍隊固然殊死拼搏,殺人盈野,一旦列強出面,雙方最後不也是和談收場,一筆勾銷了嗎?
然而,1937年蔣介石跟前兩大紅人熊式輝與陳誠,一趟上海「參謀之旅」返抵南京,回到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兩人跟蔣先生回報的內容與見解,固然南轅北轍,但是兩人卻不約而同有一個共通點,與1932年一二八事變不同,眼下,倭寇這回是來勢洶洶,志在必得。只是,兩人對和戰的看法,的確截然不同。何以致之?很多同胞會以「親日派」的標籤貼在某些人身上,但是,除了少數像汪精衛這種特殊的親日份子以外,國民政府中央或者地方軍頭,即便仍有人不贊成即刻和日本翻臉,但他們充其量只能稱之為「知日派」,而非心態上傾近倭寇的「親日派」。而這種所謂的「知日派」,事實上尤以日本軍事學校的留學生特別多,基於他們對倭寇軍事實力,和倭寇國家總體動員能力的觀察理解,他們不希望國內不明究裡的憤青們,單憑情緒性的愛國意識,把國家導引向錯誤的路途。
德國偉大的兵學家克勞塞維茲有段名言說得好:「戰爭中的一切情況都很不確實……一切行動都彷彿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線下進行的,而且,一切往往都像在雲霧裡和月光下一樣,輪廓變得很大,樣子變得稀奇古怪。這些由於光線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須靠才能去推測,或者靠幸運解決問題。因此,在對客觀情況缺乏瞭解的場合,就只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幸運了。」克勞塞維茲又說:「情報是指我們對敵人和敵國所瞭解的全部材料,是我們一切想法和行動的基礎。」然而,克勞塞維茲並沒有解釋,究竟誰夠那個資格去「靠才能去推測,或者靠幸運解決問題」。
如同克勞塞維茲所言,吾人可以體會,蔣先生明明曉得淞滬會戰開打了,但是,蔣先生內心是極其不踏實的,他深怕自己一旦做出了錯誤的戰爭決策,讓國家民族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而一旦滬戰開打,假使他即便能像貝當元帥那樣英明果決,在凡爾登戰場上投入了大批人力與物資以後,仍然守不住火線,甚而至於讓巴黎淪陷,那麼凡爾登的絞肉機戰爭便是白忙一場,法蘭西就要等著亡國滅種。他無法預估自己能不能像貝當元帥那樣,既有勇氣又有運氣!貝當擋住了德國的進攻,但是,蔣介石能不能複製貝當的經驗,他實在沒有把握!
蔣先生可以聽從法肯豪森的建議,在淞滬戰場上複製貝當元帥當年在凡爾登曾經構築的絞肉機,再在南京與上海之間,佈置一道道猶如索姆河戰役堅強如鋼鐵般的戰壕,讓倭寇活蹦亂跳的進來,血肉模糊的死在戰壕裡頭。但是,倭寇也不笨,比中國軍人更熟讀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的日本軍人,會這麼輕易跳進法肯豪森設計的鋼鐵死亡陷阱嗎?
在萬分不踏實與極度焦慮的心境下,蔣先生命令陳誠、熊式輝走一趟上海,除了「參謀旅行」,順道看看張治中的臨戰準備。直如前述,1937年8月18號,陳熊兩人風塵僕僕回到南京。熊式輝是老大哥,先開口抒發己見,熊氏的意思,依他觀察,滬上各將領及軍隊,都尚未作好臨戰準備。這位早在濟南事變吃過日本人大虧的日本陸大畢業生,體現了他對我軍的悲觀與深切憂慮。陳誠在熊式輝一派憂心忡忡之後,反倒是氣定神閒,道出他截然相反的意見了:「校長!依學生之見,天翼兄所言確是實情,但愚意,此際我軍的問題不在於能不能戰的問題,而在乎當戰不當戰的問題,假使我們今天不戰而屈,國家民族滅亡了,還不如拼死一戰,我們寧可在絕境求生,縱使今日身陷萬死之中,亦應萬死求一生,而不應坐以待斃!」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